欢迎访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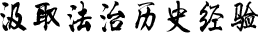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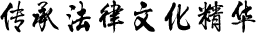
提要:唐宋之际,国家的治理方略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自唐开元年间,国家治理的重点由中央转向了地方,提出了“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治国用人原则,二是自唐中期之后至五代十国,再到宋,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及土地私有制的深入发展,国家的治理在官僚制法治的基础上,开始了司法改革的征程,司法职业化的趋向以州级检法官的全面设置为标志,以民事案件给当事人以断由为支撑,以州级司法文书“千文架阁法”为保障,开始登上了宋代的历史舞台。司法职业化之趋向的出现是宋代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也是国家政治清明的重要因素,对此进行史料的挖掘和适度的解释,是宋代司法文明叙事的一个新尝试。
关键词:唐宋州县治理; 司法职业化; 断由制度
唐宋之际,国家的治理方略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一是自唐开元年间,国家治理的重点由中央转向地方,提出了“不历州县,不拟台省”[1]的治国用人原则;二是自唐中期之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入发展及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国家的治理模式朝着官僚法制化的方向发展,[2]司法公正成为政治清明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司法职业化之倾向开始自唐宋的州县出现,尤其是宋代的州级司法,不仅组织结构严密、分工明确,而且还出现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检法议刑”制度、“断由”与“千文架阁制度”制度等。对此,学界已往的成果虽分别有所涉及,[3]但鲜有从“司法职业化”的视角看待此变化的,更没有从国家治理的高度,论证司法职业化趋向与政治清明之内在关系的。本文试论之。
一、宋代司法职业化趋向之表现
学界通常认为:司法职业化是西方法治文明特有的产物,它最基本的含义是在民主政治及权力制衡的基础上,特指司法的独立、自治与司法的专门化。这是一个基于西方法学主流价值观念的严格定义。以此定义证诸中外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前的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皆无司法职业化可言。然而,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讨论司法职业化与西方法律理性化及其与资本主义之兴起的关系时,则认为:无论是罗马时期的法学家,或者是前资本主义时期英国律师、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法注释者,都是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即司法职业化群体。[4]韦伯的视角告诉我们,对于“司法职业化”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即要把此概念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条件下分析。当然韦伯对此问题的讨论意在说明两点:首先,西方司法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及其思维方式对西方法律的理性化即形式逻辑化有着决定性影响,其次,世界各大法律系的特质,与其说由其生产方式决定,不如说由其“名流”,即各大法系中的文化传承者的价值观所决定。古典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法学家,也更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职业化。但问题在于:如若不把司法职业化仅仅与三权分立基础上的“司法独立”相联系,而是从司法官员设置的专门化及司法职权行使的制衡化两个角度出发,我们则会发现,唐宋州县的治理与司法审判出现了极其鲜明的“职业化趋向”。
(一)从“法直官”到“检法官”:宋代州级司法专门检法官员的设置
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中央的司法机构相对比较严密,尤其是到了隋唐,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作为中央三大司法机关,分工严明,职权专一,中央司法机关的职业化趋向已十分突出。唐中叶之前,无论是中央或者是地方,虽然《唐律》要求,各级司法官员断案必须引律令格式,否则就应负法律责任,受杖三十之处罚。[5]但是,各级司法机构中并没有设置专门检断法律条文、,供司法长官决断的专门官员。唐代的重要法律文献《唐六典》对中央司法机关及地方诸州的司法职能是这样记载的:“凡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稽诸证信,有可证焉而不可首实者,然后拷掠,二十日一讯之。凡断狱之官皆奉律、令、格、式正条以结之。”[6]这指的是中央司法官员。地方诸州除长官负有司法职能外,协助长官司法的诸曹官则是:“法曹、司法参军掌律、令、格、式,鞫狱定刑,督捕盗贼。”[7]这里文献中虽有“察狱之官”与“断狱之官”的差别,也有地方上“法曹”与“司法参军”的设置,但与其后宋朝“审”与“判”的严格分离仍有极大距离。唐代中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专门检索法条的司法官员,只不过这时的检法官还只限于唐代中央机关。宋初颁布的基本法典《宋刑统》载有唐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三日敕文:
“刑部法直应覆大理,及诸州府狱案,据《狱官令》,长官以外皆为佐职,法直官是佐职以下官,但合据所复覆犯由,录出科条,至于引条判断,合在曹官,法直仍开擅有与夺,因循自久,殊乖典礼。自今以后,不得更然。其诸司及外州府并宜准此。”[8]检索《国学宝典》电子文档,输入“法直”与“法直官”词条,“法直官”一词在《新唐书》卷49《志》39下出现一次,[9]“法直”在《唐律疏议》与《唐六典》中无记载,在《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上》、白居易《长庆集》卷49-50《策林》[10]均有记载,但具体设置年代有待文献证实。[11]由于“法直”与“法直官”设置的确切年代无法详考,故其职能也只好依据《唐会要》,白居易《策林》、《宋刑统》之记载,知其大略是:检索法条并参与判案。[12]这与宋代的检法官只能检索出法条、,提供判决意见,但决不能断案之职权,绝然有别。正因为如此,再加上唐中期之后,宦官把持朝政,干预司法,通晓法律的“法直”官每每借专业知识舞文弄法,致人冤屈。为纠其弊端,唐未至五代时期,朝廷开始以“格”文明确规范“法直”官的职责与权限,且要求划清“法直官”与“本断官”之间的权限,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五代后唐时期的李延范,他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据文献记载,后唐长兴二年(931)八月十一日,大理卿李延范奏:
“当寺今有要切事节,谨具诸件如后:一件,寺司每奉敕旨断案,准格须顺委法直司据罪人所犯,检定法条,本断官将所犯罪名,并所检法律及法书本卷,对验不差,然后逐件于法状上署名,下法定断。伏见寺司案内,每将法直官所检条件法状,备录在详断案。伏准格文,法直官只合录出科条,备勘押入案,至于引条判断,合在曹官。”[13]这里的“法直司”就是指的“法直”或“法直官”;“本断官”与“曹官”即是指专门负责依据法条决断案件的判案官员,前者专门负责依据罪名检索出适用的法条,后者则依据“法直”所检之法条进行断案,二者职责分工明确,不得侵袭。因为法律要求判状内不许“载法直官姓名者”。[14]
问题在于后唐时期,虽然出现了职权分明的检法官员——“法直”,但却依然局限在司法机关——大理寺所断案件中,大理寺审断的是京师及地方上报来的大案,至于地方的审判机关仍无专门检法官员的设置,到了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二月,天下诸道州府出现了专职的“检法官”。史称:“今后应天下诸道州府断遣死罪者,候断遣讫,录元案闻奏,仍分明录推司官典及详断检法官姓名。其检用断法条朱书,不得漏落。”[15]
台湾学者陈登武先生认为,这条史料为以往学界所忽视,其实它是宋代“鞫谳分司”制度的先声。此处的“推司官典”与“详断检法官”正是宋朝的“鞫司”与“谳司”,即“法司”的前身。问题是,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骄兵悍将当政,司法的残酷与刑狱的黑暗使“推司”与“检法官”职权的划分无实际意义。真正意义上的专职“检法官”,普遍设立于全国各州,并以制度(如检法官的充任资格、升转、奖惩、地位、职权等)为保证使其行使职权,则是两宋之事了。
宋朝建国伊始,太祖、太宗就十分重视法制建设,表现在司法上,除了以读书之士子取代五代之马步牙校充当司法官员外,其次一个最大的举动就是严密州级司法组织,于全国各州设置专门负责“检法议刑”的官员——“司法参军”,实行“鞫谳分司”制度。
《宋史》卷167《志》120《府、州、军、监》《幕职诸曹官》称:“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司理参军掌讼狱勘鞫之事。”这里的“司法参军”与“司理参军”是州长官——知州的属官。宋制,全国地方上置州县二级行政机构,长官由朝廷委派,以京朝官充任,谓知州、知县。州上边有路的设置,是监察机构,与州同级的还有府、军、监,其中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稍重,如开封府、大名府等。依据宋代法律规定,县只能判决徒刑以下案件,即笞杖刑的轻罪及婚姻田土之类的民事纠纷案件。徒以上案件,可拟判,但判决权在州不在县,故州一级司法权力较大。鉴于五代十国刑狱黑暗、滥杀无辜的教训,宋朝特别重视州一级的司法建设。
按照宋代法律之规定,知州、知县作为亲民之官,必须亲决囚徒,违者徒二年。[16]故知州作为长官权力重大,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再加之知州、知县司法、行政职务兼于一身,事务冗杂,宋代于州级长官之下,特设幕职官与诸曹官承办长官交派的各种司法业务。幕职官与诸曹官史称“州县幕职官”,前者有“签书判官厅公事、两使、防、团、军事推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等,后者则指“司法、司理、司户”参军诸曹官,所谓“诸曹”就是指专门负责承办各项业务的机构。宋代司法职业化之趋向在地方上的重要表现就在于“检法议刑”制度确立,因为它是宋代另一别具特色制度“鞫谳分司制”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均设有负责“检法”的官员,中央除了三大司法机关的“检法官”之设置与司法审判相关外,其它机关——如户部、三司使等部门之“检法官”,与司法审判并无关系,他们只是负责检索与该部业务相关的法条而已。我们在此讨论的重点是州级司法审判中司法参军之设立及其职权的范围。必须明确的是,“司法参军”作为州级属官,早在唐朝便已设立,并非是宋朝首创,但使其职权专业化,即专管“检法议刑”,不得参预审理与断决,则是宋朝所独具的时代特色。宋代州级司法,在长官之下设有“鞫司”与“谳司”,又称“推司”与“法司”。“鞫司”或“推司”,相当于现代的侦讯与预审,“谳司”或“法司”相当于现代的判决机构。按照宋代法律之规定,不仅审讯与判决要分立,职权不得混淆,更不准相互打探消息以屈法营私。就是法司的判决中,也须由通晓法律的专职人员——检法官,州一级即“司法参军”,专门负责依照犯人之罪名检索出本案所适用的法条,并依据法条提出刑罚之建议,这就叫“检法议刑”。“议刑”只是提出建议,并非是决断,因为判决权在长官。故州之“司法参军”的专职是:检出法条,提出建议。这样以来,宋代州级司法实际是两大阶段,三个程序,两大阶段是:审讯侦办与判决,三个阶段是:(1)侦审或叫“鞫推”;(2)“检法议刑”,即检出法条,提出建议;(3)依法判决。往往由长官做出,并鎋印发布公告。宋代把这种制度称为“鞫谳分司制”。对“鞫谳分司”制度,学界讨论颇详,本文不再赘述。我在这里关注的是如何从司法职业化之趋向考察唐宋州县治理的经验,故司法参军之专职检法的具体表现及其效用,自当在考察视野之中。让人颇感欣慰的是,幸有《名公书判清明集》保留的真实案例及《宋代石刻文献》的记录,使我们尚能在千年后一窥司法参军之检法与法官判决职权分立之风尚。
(二)从《清明集》中的“司法拟”看宋代地方司法职业化之趋向
《名公书判清明集》[17]是一部反映南宋后期社会生活与司法审判制度的宝贵历史文献,其文献价值与反映宋代司法制度的深度一向为学界所重视,但从“检法拟”之角度,看宋代司法职业化之趋向,并由此评判其历史地位,还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这里试加以检讨,以补学界研究之不足。
《清明集》一书收有五份南宋时司法参军所拟的书判,史称“检法拟”。[18]它真实的反映了“司法参军”作为州级司法属官,在具体的历史案件中所履行的“检法议刑”功能。之所以叫“拟”,不叫“判”,亦不称为“断”,是因为“判”或“断”是长官的职权,司法参军只能依案情,检出适用于此案的法律条文,提出适用何种刑罚或某种处罚的建议,故叫“议刑”,也称作“拟判”。这里拟选两件以便分析,一为民事,一为刑事。前者为家庭财产之争讼,书判名为“立继有据不为户绝”;后者为与官方勾结强取钱财的刑事案件,书判称之为“结托州县蓄养罢吏配军夺人之产罪恶盈贯”。
先看家庭争财案。时间为南宋中后期,地点是荆湖北路的通城县(今属湖北省咸宁通城县)。案情是:吴琛有四女和一抱养子,各为“二十四娘”、“二十五娘”、“二七娘”与“二十八娘”,抱养子名为吴有龙,又称二十六郎。二十四娘与二十五娘皆已完婚,但并未出嫁,因为她们二人都是“倒插门”,即招的“赘婿”,三女二十七娘具体情况不详,案中记载,或嫁给了许氏,或卖为“义女”,但因人在外地,真假难辨。二十八娘为幼女,尚未到出嫁年龄。争讼的原因在于:吴琛及养子吴有龙双双死亡,吴有龙之子吴登及母亲不能使家庭和睦,遂使已到婚嫁年龄的二十八娘兴讼到官,要求依《户绝法》重新分割家庭财产。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吴琛死后,其家庭是否为户绝。唐宋时,户绝的含义相同。所谓“户绝”,又称绝户,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父系子嗣的断绝,即无后者为户绝,二是指纳税单位“户”的消失。一个有男性家长的户称之为“课户”,一个无子嗣(子嗣包括亲生、领养、立嗣)的寡妇家庭则为“女户”,其死后就成为绝户。白凯说:“从国家的观点来看,绝户同时意味着父系的断绝和纳税单位的消失。因此,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兄弟数人同居未分,共同拥有财产的家庭,即使其中有一个兄弟(及其妻)已死而无子嗣,该户仍是一个完整的纳税单位,国家并不将其看作一个绝户。因此绝户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这样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父亲已经与他的兄弟分家并独立门户,而父亲(和母亲)已去世,没有留下子嗣,这样的家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绝户,即父系的断绝和纳税单位的消失”。[19]
就本案来说,吴琛虽无亲生儿子,却有一养子,他是户绝吗?我们先来看宋代的法律规定。宋代,男姓家庭若无亲生子,可以立嗣,也可以抱养异姓子。立嗣分两种情况,一是立继,二是命继。宋代不同于其它朝代,立继是指一个男性家长年老无子时,由他过继一个同宗昭穆相当的男子为自己的嗣子,或在其死后,由其寡妻过继一个嗣子,这两种情况都叫立嗣,但其法律地位却有差异。立继之嗣子法律地位同亲生子,命继则是指当男姓家庭家长夫妻双亡,生前无立继的情况下,其族人为其过继嗣子的行为。命继子法律地位低于立继子,他只能与户绝之家的女儿及国家共同分割户绝之财产。对于一个无男姓子嗣的家庭来说,若男姓家长生前无立继,他也可以抱养一个异姓子为自己的子嗣,这种情况称为“义子”。义子若要获得如同立继子一样的权利,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异姓子须在三岁以下,二是抱养过来后,必须办理法律手续。即向官府申请,除去抱养子家庭所在户口,归于抱养之家。同时由异姓改为抱养家庭之姓,法律上谓之“附籍”。附籍之法是比照“除附法”实行的。
就本案而言,吴琛之长女、次女皆招赘婿,本可以不再抱养义子,可是吴琛似乎并不觉得两个女婿可靠,遂抱养异姓子有龙为义子,并比照“除附”法办理了有关手续,可谓是完全符合法律之规定。而且,依儒家礼制精神,有龙改姓之后还于吴琛死时行了“斩衰”之礼,即服丧三年。这更从法律与礼制两方面说明了有龙的嗣子身份完全成立。怎么可以说吴有龙不是吴琛之子,吴琛是户绝呢?况且,现在吴琛、吴有龙皆已去世,去世多年未有事端,现何以成讼呢?原因在于有龙之子吴革与其母亲没有很好的对待未出嫁的二十八娘,致使二十八娘出走,并告之官府,同时次女之婿胡闉也声称,吴氏之家产,其中一部分是由吴家二婿以妻家之财物,营运增殖而成,因此要求这部分财产重新分配。
归纳本案的焦点有四:一是吴琛之家是否户绝?二是应龙是否享有亲子之待遇?三是胡闉之诉是否成立?四是本案适用的法条有哪些?作为检法的司法参军,是怎样根据法条与案情提出审理意见的?
由于第一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相互联系,故可以合并分析。吴琛有四女无亲生儿子,若不立嗣或收养异姓子,就会成为绝户。根据案情看,吴琛生前没有立嗣,也没有命继,而是于生前抱养了一个异姓子。宋代,抱养异姓性若符合法定条件,并办理有关手续,其法律地位与亲子同。这个异姓子是否符法律规定的条件呢?宋代法律规定了两项条件,一是异姓子之抱养时年龄须在三岁以下,二是比照“除附法”办理附籍手续。对于吴有龙之身份,判词称,案发时查得县所给证据有二本,一是存在吴琳之处的,所记为七岁。吴琳为何人,判词中无明确说明,或者是吴琛的兄弟,总之是与本案有关联的人。以此为据,异姓男吴有龙所立就不合法律规定,因为他已经七岁;二是阿涂之据,记载为一岁。阿涂是谁,判词中也无说明,推测应是吴登之母,亦即吴有龙之妻。按此所载,符合法律规定。到底谁为真呢?“司法拟”分析为:前者为假,后者为真。理由是:首先,吴琳之据文字有改动痕迹,七字为改字;其次,有龙若是七岁,公法不当立,县司也无理由给付证据,就不会有阿涂手中记载为一岁之公据,故“司法拟”判定为,有龙被抱养时一岁为真。这就符合了法律之第一项规定。第二条规定,办理“附籍”手续,即除去有龙原户籍,并改姓归于吴琛户籍之中。这项手续办完,依宋代法律,吴有龙就由“义男”成为吴琛嗣子,享有亲生儿子的地位。本案中所说的依法都是哪些法呢?
“司法拟”在本案中捡出的法条如下:
第一,诉讼时效,即“诸义子被论诉及自陈之法”。本案是在吴琛(养父)及吴有龙(养子)均已死亡数年后,才由吴琛幼女(二十八娘)及其姐夫到官府告状的,先不说二十八娘及其姐夫胡闉有无告状资格,[20]单就诉讼时效而言,“司法拟”捡出的法律条文是,“在法:诸义子孙所养祖父母,女母俱亡,或本身虽存,而生前所养祖父母、父母俱亡,被论诉及自陈者,官司不得受理。”就本案而言,吴有龙与吴登本是义子孙,只不过办理有关法律手续后,其法律地位视为吴姓亲子,其实,这只是法律上的拟制,并非他们就是吴琛亲生子孙。法律在此种情况下,因涉及到三方的权益,即养父家、生父家与义子及其后人,故法律必须在三家权益的保护上寻求平衡点,否则就会引起一系列麻烦。宋代法律既要保护养父母之权益,也要保护生父母权益,还要保护义子之权益。从反面来讲,法律之设计既要防止生父家借送养之名,不尽养子之道,不办理有关手续,而行觊觎钱财之心,也要防止养父家在时过境迁后,不承认养子之法律地位,而无端追诉养子的身份。故法律规定两种情况下,不再受理养子身份认定之诉讼,一是养子与所养祖父母、父母俱亡,二是养子在世,但其所养祖父母、父母俱亡。结合本案,正是符合第一种情况。吴有龙不仅身份合法,且已在养父吴琛死后,恪尽为子之道,行了“斩衰”之丧礼,故吴琛家不是户绝,吴有龙具有亲子之法律地位。
第二,“异姓养子与除附法”。司法检出的法条是:“又准法:异姓三岁以下,并听收养,即从其姓,听养子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虽不经除附,而官司勘验得实者,依法。”[21]何谓“除附法”?《清明集》卷之八《夫亡而有养子不得谓之户绝》的判词说:“此谓人家养同宗子,两户各有人户,甲户无子,养乙户之子以为子,则除乙户子名籍,而附之于甲户,所以谓之除附。”[22]由此可知,“除附”仅适用于养同宗子,异姓子虽不适用“除附法”,但可比照施行,即经官司(多为当事人所在地区的官府)勘验得实后,依“除附法之文”。就吴氏女争讼之案而言,案中吴有龙,原姓闾丘,为异姓子。虽不经除附,但经养父吴琛提出申请后,由县衙查验得实,给据为凭,其程序是比照除附法实行的,其法律地位是依照亲子孙法获得的。
第三,赘婿以妻之财营运增殖“分配法”。“司法拟”判词检出的是一条宋廷频布的敕令:“在法:诸赘婿以妻家财物营运,增置财产,至户绝日,给赘婿三分。”[23]这道法令颁布于何时?具体记载不详,欲理解它,先须了解宋代中国家庭财产的性质。唐宋时期,实行“同居共财制”,此制度下,家庭财产之属性为“家产”,即是说,家产既不归父亲个人所有,也不归家中某个子女所有,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共有”,因为古人没有民事权利主体之概念,而是为“家”所有,对此学界已辨之甚详。[24]问题在于,到了宋朝的仁宗年间,政府为了适应社会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社会生活之所需,特于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正月乙未下诏:“应祖父母、,父母服阕阙[25]后,不以同居异居,非因祖父母[父母]财及因官自置财产,不在论分之限。”[26]台湾学者柳立言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诏令,因为它把个人从家庭财产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27]法令赋于个人具有私财的权利,即家庭中的儿子或女儿可以拥有私财。既然女儿有私财之权,女儿之丈夫——赘婿在岳父家依靠妻子之财,营运增殖后,自然也有权分取其利,故在判词中,吴琛之女婿胡闉便借二十八娘告讼之际,要重新分配吴琛所留之家产,因为此家产中有部分财产是自己依靠二十五娘之嫁妆增殖的。但欲分此份家产,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吴琛须是“户绝”,即法律中所谓“至户绝日,给赘婿三分”。前面已经言明,吴琛已经以“义子”吴有龙为继子,当然不是“户绝”,胡闉之要求自然被法官所否定。
第四,“户绝财产与在室女法”。即:“又法:诸户绝财产尽给在堂诸女,归宗者减半”[28]本案中,司法检出此法条之用意在于告诫二十四,二十五娘及其二人的丈夫石高与胡闉,吴琛非户绝之家,吴有龙非义子,而是父亲吴琛所抱养之继子。继子权利与亲子同,吴有龙之子吴登是吴家的承分人,吴家香火由吴登延续,吴家财产也由吴登继承。二十四娘与二十五娘作为女儿,已在婚嫁时,依法律取得嫁资,父亲死后也已分家,现在理应与丈夫一起“扶颠持危”,续吴氏之血脉,帮助吴登重振家业,不应再有分外之心。
第五,“在室女听婚嫁之法”,按照宋代法律,男姓性家长辞世时,若有儿子,财产由儿子继承,女儿给嫁资,嫁资之数目为兄弟聘财之半。南宋时,法律有所变化,既女儿有权获得兄弟所继承财产的二分之一,称为“男二女一法”或称“男倍女半法”[29]就本案而言,吴琛四女中,长女次女已嫁,三女或称已嫁许氏,或称卖为义女,实情不详。幼女二十八娘已到婚嫁年龄,却未得到应有的嫁资,而且因与吴登母子所处不和,居住在吴琳之家,吴琳身份不详,似是吴琛之兄弟,故司法提出的建议是:监督吴登母子把二十八娘迎接回家,好好照顾,尽姑侄之礼,待日后择偶后,选择吉日出嫁,照法给嫁资。司法捡出的法条是“在室女婚嫁法”中的一部分,即“在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至于嫁资之数,由于前有两个姐姐嫁资可比,故司法并未列出,想必是在有例可循的前提下,自然不难处理。至此,司法针对本案所检的法条有五:(1)诸异姓养子身份追诉时效法,(2)异姓养子与“除附法”,(3)赘婿以妻之财营运养殖分配法,(4)户绝财产与在室女法,(5)在室女听婚嫁法。
尽管本案中的司法参军在赵知县判决的基础上,对案情分析的鞭辟入微,头头是道,而且一一检出法条,其专业化程度是十分令人惊叹的!然而,在宋代的司法程序中,司法参军只能依案情检出法条,发表建议,但却不能做出判决,所以他最后只能说:“管见如此,取台判”。[30]所谓取台判,就是最后由州长官定夺,可见检法与判决是两分的。
《清明集》中,司法参军的拟判及检出来的法条,既有民事的,如本案。也有刑事的,如《清明集》卷12《结托州县蓄养罢吏配军夺人之产罪恶贯盈》、《与贪令捃摭乡里私事用配军为爪牙丰殖归己》;[31]有州司法参军所检所拟,也有路(监司)司法参军所检所拟,检即是检出法条,拟便是拟判,或称“议”。不论是哪种情况,都只能说明宋代地方司法参军的职责是“检法议刑”,它是宋代地方司法,尤其是州级司法中的一个专门化很强的环节,它不能参与审讯,也不能最后判决,只能检出法条,提出建议。这并非是停留在纸面上理论,而是真实的司法实践。《清明集》提供的判词便是检法与判决两分之最真实可靠的实据。
(三)宋代地方审判,即州级审判中“侦讯、检法、判决”三分,这是司法职业化趋向的典型表现
南宋司法官员周林曾说:“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32]这就是宋代刑事审判中所实行的“鞫谳分司制”。“鞫”是指审讯,“谳”是指判决,“鞫谳分司制”就是指审与判的分立。关于此制度的讨论,学界已发表有大量的成果,台湾学者徐道邻,,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大陆学者戴建国、王云海均在其论著有所论述。这其中需要关注的是戴建国教授的研究,因为戴建国先生针对徐道邻与宫崎市定所遇到的问题,即在同一个司法官员身兼数职的情况下,宋代所实行的“鞫谳分司”制度是否还有效?戴建国回答了此问题。戴认为:一个司法官员身兼数职时,并非说“鞫谳分司制”就不实行了。这是因为“鞫谳分司”是指审与判的分立,一般来说,这种分权精神落实到司法上,必然是司法官员职权的专门化。但由于宋代全国形势的复杂及其官员设置数量的限制,在一些边远地区,一官多职经常出现,这是因为要提高司法效力,就不能于人数极少的县或州对官员专职专设,而是一官数任。此种情况下,“鞫谳分司制”精神如何落实到位呢?戴指出,这种情况下依然实行分司制,就在于官员于集体案件中,一旦被委任去履行某种职责时,他所兼的其他司法职权就不能再行使。譬如说,“某位官员被任命为某州的录事参军兼司法参军时,这位官员的职责除了主持州院事物外,也可以担任案件的检法议刑工作,但在实际审判中,如果这位官员被派去审讯犯人,依据鞫谳分司原则,这位官员便不能同时再担任同一案的检法议刑工作。[33]戴建国的分析极为深入,但是这里仍需要指出以下两点:第一,宋代州以上直至中央实行的鞫谳分司制,实际上包含了四个小阶段,也可称之为程序。首先是,刑案发生后,抓捕与审讯属于第一个环节,宋代称之为“巡捕”。所谓巡捕,又称侦捕,盗捕。指侦查与逮捕嫌疑犯,宋代由巡检与县尉负责,简称为巡尉。巡捕抓获犯罪嫌疑人后,须交由专门的人员审讯,这就是第二个环节,“推鞫”,又称鞫狱或勘鞫,即对捕获之犯罪嫌疑人进行事实调查与讯问。此项工作由狱司负责,史称狱司推鞫,在州由司理参军,或被称为“狱官”的录事参军负责。案情基本审理清楚后,便转交到了下一步,即第三个环节,“检断”。所谓检断,是检法议刑的简称。宋制,州设司法参军专门负责检索法律,并分析案情,提出司法建议。待此项工作完成后,案子便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即第四个阶段——判决。宋代,州的司法权甚重,即州长官有权断决徒刑以上的案件,故其组织非常严密,审判程序分明,司法原则独居时代特色。第二,如果说,“检法官”之设置与职能行使体现了宋代州一级司法之专业精神的话,那么上述层次分明的审判程序则从分权制衡的角度,反应了宋代州级司法的职业化趋向。
第三,司法职业化一般来说是与专职专设联系起来的,宋代也是如此。多数情况下,宋代州一级的司法参军专管检索法律,分析案情,但有时也会出现兼职的情况,如南宋时司法参军监管州里的粮仓与财政,这是本官兼它职。也有可能出现它官兼本职,即不是专管检法的官员负责检法,如州的录事参军,本职为主持州之院务,审理州狱,有时也兼“检法”职能。上述两种情况之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宋代州级司法的职业化趋向,因为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一旦兼职的司法官员职责被锁定,他它的兼职便不再在履行,兼职与司法职业化表面相反而实相成。这说明专职是司法职业化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要条件。
二、审理民事案件,宋代于县衙创立了独有的给“断由”制度
县令是古代的“亲民之官”,尽管《唐六典》对县令的职责做了详尽规定,且要求其重在“抚字黎氓,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34]但唐中期之前,州县之用人并非是唐朝的重点,直到唐开元年间,唐朝才把对人才的选拔由中央转向地方,提出了“不历州县不拟台省”[35]的用人原则。尽管如此,由于唐中期之后,社会的变革及藩镇割据势力强大,地方用人率由节度使自辟,中央遂失地方用人之权,其政策自然难于贯彻,及至五代,县令率由武人充任,其吏风贪黩,司法严酷向为史书所病。宋自建国伊始,便惩五代十国之弊,于司法进行改革。其主要措施有:其一,州县长吏多用士人,其二,地方司法官员设专职,且要求他们参加法律考试,并具有司法实践经验。使司法朝着职业化方向发展。
宋室南渡以后,随着江南私有制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从民间崛起,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多元利益于社会结构中呈现,诉讼之风遂兴起于江南各地。宋政府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之需,不得不把司法的重点由刑事转向民事,即由原来的“狱讼为首务”转向“治理以民事为急”,这种精神反映在南宋的县级司法上,就是创立了宋朝独具的“婚田之讼”,必给当事人以“断由”的制度。
对于南宋的“断由”,我已于近年的研究中多所论及,[36]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此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即断由制度还应与宋代司法职业化趋向密切相关。之所以这样说,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断由”的形式属性,而在于“断由”背后所反映出来宋朝政府对县令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专业化诉求。在宋政府看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婚田之诉”,直接关系到社会生活中民众矛盾的化解与政策的安稳,如果一个“亲民之官”不能公正的审理所在地的民事纠纷,老百姓就会心怀愤恨之情,或诉之于州,或诉于监司,直至朝廷,这样不但使国家的司法资源白白浪费,而且也使矛盾加剧,积怨加深,小则邻里不和,大则演化为人命大案,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故宋代朝廷不断发布敕令,要求断案之长官,必须给诉讼当事人以“断由”,以求司法公正。由于“断由”需要明确记载案情及适用的法律条文,乃至法官判案的依据及其道理,故其制度的施行必然要求审案者要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及法律专业知识,糊涂断案是无法给当事人明确的理由的。
我们先来看宋代原始文献对“断由”的解释,再来看一个南宋时期的县令对为何要给“断由”所做的内心独白,最后再把“断由”置身于宋代社会生活的脉络中与百姓过日子的规则及逻辑相联系,以理解“断由”在司法职业化中的作用。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宋朝首创给当事人以“断由”的制度。史载:“绍兴二十二年辛丑,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言:‘比来遐方多有健诉之人,欺绐良民,舞玩文法。州县漕宪未结绝,则伸冤于部,于台,于省,官司眩于偏词,必与之移送重定,外方往往观望,为之变易曲直。欲今后所讼送,如婚田、,差役之类,曾经结绝,官司须具情与法叙述定夺因依,谓之断由。人给一本,厥有翻异,仰缴所结断由于状首,不然不受理,使官司得以参照批判,不失轻重,而小人之情状不可掩矣。将来事符前断,则痛与惩治。可使户婚讼简,台省事稀,亦无讼之一策也。’上曰:‘“自来应人户陈诉,自县结绝,不当,然后经州,经监司,以至于经台,然后到省。今三吴人,多是径直至省,如此则朝廷事多,可其所奏。’”[37]
这段史料生动地记载了南宋高宗与右谏议大夫林大鼐之间就为何给断由、,断由是什么的对话。就时间而言,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辛丑,印正于《宋会要辑稿·刑法三·诉讼》,知是公元1152年5月7日。事情的原委是三吴之地婚田诉讼繁多,因得不到有效处理,当事人径自诉之于州洲,未及审理完毕。又诉之于中央司法机构,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司法秩序,引起了朝廷的高度关注,才有了这番对话。文中的“三吴”之地,并无确切可指,大概指现代的江苏与浙江。其实,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因为当时南宋的江南各路均有此类现象之发生,此从宋人的各类材料中可以验证。
概括说来,“断由”应是南宋民事审理中的专有名词,质言之就是判决理由,当然就其形式而言,你也可以说它是由官府制作的、,记载案情与适用的法律条文及其判决理由的法律文书。由于时代的遥远,宋代这种发给当事人的法律文书或凭证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通过《清明集》之判词及其他宋代史料之叙述,我们仍然可从中知其大概。
断由的作用,我曾在《释干照》与《宋代司法传统的叙事及其意义》之文中加以概括,现在这种概括依然有效。简言之有三:
第一,断由作为法律文书,它记载了基本案情、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与法官的逻辑推理、案情分析与判决理由。它对案件的真实与公平与否,起着证信的作用。其次,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断由”为据向上级司法机关申诉。宋代没有三级二审制或四级三审制的概念,法律的既判力不可能如现代社会一样清晰,故上诉与申诉没有什么界限,不服判决即可上告,宋代称作“翻诉”,既便是婚姻田土诉讼,一个案件审理三至五次是宋代司法中常见的现象,甚至可达七八次之多,缠讼数十年之久,《清明集》一书对此多有记载。断由因此成为上级机关审理及查明案情的重要依据。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通过给当事人以“断由”的制度,既表明了宋代政府对民事案件的重视,同时,也是对县令法律素养的高水平要求。南宋时,临湘县令王炎留下了一篇极其难得的审理心得。他说,临湘与江浙一带大县相比,地狭民稀,词讼也只是这些“繁难之县”的百分之一。即便如此,临湘县的诉讼案件仍有一半是争田地的。可见,田畴官司是百姓生活中常见之现象。既然讼田如此之多,说明田产之争对于百姓来说该是多么的重要,那么,作为亲民之官的县令该如何审理呢?
王炎认为,审理田产之讼,首先要看“干照”。干照既是田产交易的一应契约文书,这说明宋代审理田产案件,书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若契约文书明晰,就再进一步看,现在所争田产究竟由谁管理、占有、使用。如果契约涣患漫不明,田产归属之诉的追诉时效限于二十年。若因战乱及自然灾害,原田主人已逃离,土地已荒芜数十年,现在有人开荒田为熟田,则原主人不得执旧田产证予以“刬夺”。若当事人争执不休,谁管业谁开荒,难以见虚实,那么审理者就必须问及邻保,细细调查,方得其情。
这是通常的情况,审理原则十分清楚,问题是临湘县虽小,可民情万端,所争田产之讼自有与他县不同之处?王炎列出的特点是:(1)契约不明,田产界限相互交叉,有的人一直纳田税,可并无田产证明;(2)有的既不纳田税,也无田产证明,却一直在占有、使用。在此种复杂情况下,县令只能依据法律精神、,根据案情,平心据理而断,既不敢徇私、,偏颇袒护,也不能尽听胥吏之偏词,受其迷惑。若当事人反复争执,则必须要求原被告至庭前问话,反复诘问、,论辩,但不得施以刑讯,也不得把他们收监拘押。
即便如以上如此小心,但案情复杂,人心不古,法官也恐有“十得一失”之弊。对此,县令断案时又必须依据法律之规定,为当事人出具“断由”。王炎说:“然人之情伪固难尽知,而一己所见岂能尽当,即又准条令为给断由,其断由之中必详具两争人所供状词,然后及于理断曲直情理,恐人户以为所断未公,即当执出断由,上诣台府陈诉。”[38]
在这段文字中,王炎作为临湘县县令,把审理民田之讼之所以给当事人以断由的原因及作用都做了说明。究其原因,王炎概括了两点:一是怕自己谋虑有误,以失公平,二是怕当事人故意找茬子不服而缠讼,给出断由以为上级审查凭证,因为断由之中,已记载了诉讼双方争执的原因及判决的理由。
王炎所述,确实道出了一个南宋亲民之官的心声。但若从宋代社会生活的发展脉络而言,无论是“断由”作为民事审判的专有名词,或者是“给断由”作为一项民事诉讼的制度,它之所以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单独出现在南宋,既跟给宋朝政府为适应社会生活发展之需要而采取的重大措施密切相关,也与百姓生活中对司法专业化的诉讼相关。首先是朝廷针对社会上连年出现的“讼累”而采取的社会减压措施,所谓“讼累”,既包括了当事人在讼师教唆下的兴讼与“健讼”,也包括了当事人不经州县而径直诉讼至路乃至中央的“越诉”。其次,是宋政府试图通过民事诉讼给当事人以“断由”的措施,来提高办案的效力,以强化南宋地方司法官员的法律素养,并满足南宋百姓社会生活中对司法专业化的诉求。南宋时,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及土地权利的细密化,典、卖、租乃至以田宅质押借钱等各种不动产交易现象在宋代百姓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出现,由此产生的田宅诉讼也日益增多。在百姓的生活中,不仅田宅交易需凭契约文书已成为时代风尚,就是打官司需要讼师帮助也成为普遍现象。在社会双重的压力之下,田产之讼不仅要求法官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同时,老百姓对司法公平的要求也越来越紧迫。他们不仅渴望法官明断是非,还要求法官判决不能拖延时日,以免案牍积压,既妨碍农务,也影响当事人对司法清明的心理诉求。所以南宋自高宗以后,不断颁布诏令,严禁断案不给断由,甚至对给断由的时限不断地的进行给予调整,或当厅给予断由,或三日后给断由。且看以下史料:
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六月十四日,臣僚言:“州县遇民讼之结绝,必给断由,非固为是文具,上以见听讼者之不苟简,下以使讼者之有所据,皆所以为无讼之道也。比年以来,州县或有不肯出给断由之处,盖其听讼之际,不能公平,所以隐而不给。其被冤之人或经上司陈理,则上司以谓无断由而不肯受理,如此则下不能伸其理,上不为雪其冤,则下民抑郁之情皆无所而诉也。乞诸路监司、郡邑自今后人户应有争讼结绝,仰当厅出给断由,付两争人收执,以为将来凭据。如元官司不肯出给断由,许令人户径诣上司陈理,其上司即不得以无断由不为受理,仍就状判索元处断由。如元官司不肯缴激纳,那即是显有情弊,自合追上乘承行吏人重行断判决”,从之。[39]
上文已述,民事诉讼给当事人以断由的制度,是自高宗绍兴二十二年(即公元1152年)开始的,然从孝宗绍熙元年的这道诏令看,州县审理民事诉讼于结案时,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法令,其中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的原因是某些州县因民讼繁多,不能按时结绝或者是判决不公、,故意隐而不给,这才引起朝廷注意,要求诸路监司及州县从此以后,民事案件于审理结案时,必须当厅给当事人以断由。如若不给,许令当事人越级上诉,上级司法机构不得以无断由为理由不接受词状。即是说,上一级司法机关必须受理,而且还要继续向原断机关索取断由,若原断法司不肯出具“断由”,则推定为审理有作弊之嫌,原断机关长官与办案人员即要受惩处。这是一道更加严厉与详实的法令。
“当厅给断由”是一项严格的要求,而且这只能适用于那些案件事实清晰,不需要追索证人的轻微民事案件。对于案情复杂,又需追索证人的民事案件是无法当日审结的,自然也就给不了断由,所以后来,朝廷又有三日给断由之谕。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三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乞申严旧法,行下诸路,应讼事照条限结绝,限三日内即与出给断由。如过限不给,许人户陈诉。从之。”
由于“给断由”之制度既涉及到路、州、县各级司法机关,又关涉到案情的轻重各不相同,故宋政府曾把不同时期的诏令,归纳整理,整齐画一到《庆元令》中,其具体规定是:凡是县所受理的轻微民事案件,限当日结清,并当厅给断由于当事人;若需追索人证、物证,原则上五天结案;州郡限十日;监司半月为限。有其它重大原因者,不在此限。各级司法机关若无故违限,许人户陈诉,并追究司法机关之责任。[40]这是宋代历史文献中能见到的最为详实的有关给断由的规定。
三、宋代以“千文架阁法”管理司法文书,为地方州县司法的职业化发展提供了保障
中国是一个成文法传统极其悠久的国家,自春秋战国以来,公布成文法便是一个历史大趋势。秦汉统一中国后,历朝历代皆有统一的法典颁行于天下。尤其到了唐宋,不仅有《唐律疏议》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影响于后世及周边各国,而且宋还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大规模地的颁布敕令、,修订敕令。北宋有元丰敕令的修订,南宋则有《庆元条法事类》颁行于全国。如此大规模的修订法令,必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建立起司法文书与法令的管理机构,并制定详尽的档案管理制度,来保证司法职业化的运行与实施。中国的档案管理机构与制度到宋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学界通常认为,有宋一代,从北宋真宗时起,已开始于京城设立专门的架阁库,管理档案。档案学专家王金玉教授曾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专著《宋代档案管理研究》,并于《历史研究》上发表大作《宋代千文架阁法辨析》,[41]专门研讨宋代地方上“千文架阁法”的实施。根据王先生的研究,“架阁”一词原指贮存文牍案卷的橱架。延伸之,可指架阁库、架阁官,也可指将档案放在橱架上保存之意。如宋代文献中多有‘置库架阁’、‘送库架阁’、‘别库架阁’语。‘千文架阁法’应即以《千字文》编排字号收贮档案的方法。《庆元条法事类》文书门架阁目中规定,仓库的销钞薄要“常留一纸以《千字文》为号,月以架阁。”[42]
宋代的地方档案库之创立并非始于宋仁宗时期的周湛,而“千文架阁法”之创立则始自于周湛无疑。对此,档案学界辨之已详,不必赘述。现在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宋代地方档案库之设立与司法职业化倾向之内在关系。简言之,正是唐宋之际从中央到地方之档案制度的完善与档案库的建立,才从外部支撑了唐宋时期州县司法职业化倾向的出现,甚至可以说,如若没有档案库的建立,司法参军或其它各机构中的检法官员,欲从卷帙浩瀚的法令文书中检索出具体案件中适用的法令,无疑是大海捞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因为宋代地方州县各级档案库的建立,尤其是周湛“千文架阁法”[43]的推行,才使得检法官于法律文书中检索出法条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由于史料的散佚及历史长河中文献的湮灭,宋代地方上架阁库实行中,检法官从中检索法条的直接史例已无从查考。但我们已然可以从《庆元条法事类》残留下的《文书门·架阁敕令格》中,窥视到宋代架阁法的蛛丝马迹,并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对架阁官员职责的设置:
诸架阁库,州职官一员,县令丞、簙簿掌之。应文书印缝计帐数,封题年月事目并簿簙历之类,各以年月次序注籍,立号编排(造帐文书、别库架阁),仍置籍。遇借,监官立限,批注交受,纳日勾销,按察及季点官点检。[44]
诸制书若官文书应长留而不别库架阁,或因检简移到而不别注于籍者,各杖仗一百。即应检简公案而被差覆复检官不如令者,罪亦如之。
诸架阁库文书,所掌官吏散失者,杖一百。(散,谓出限或不立限各过百日不拘收者。行遣不绝者非。)当职官吏以架阁应留文书费用者,以违制论,非重害减三等。[45]
从上列材料中可以看出,宋代法令对架阁库官员的职责及其失职所应承担的责任都作了详尽的规定,法令及其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纳税簿籍,司法文书等属于法律上规定的“重害文书”,保留时间长,而且要求及时晾晒,以防霉变。严密的档案管理制度为检法官适时检出法条,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而此点尚未被学界研究所提及,有必要予以表出,以示重要。
宋代检法官在民事诉讼中于架阁库司法文书中检出的法条除了《清明集》中保留下来的“司法拟”外,尚有《宋代时刻文献全编》二册《江苏通志稿·金石十五》《给复学田公牒二》记载了宋理宗绍定三年(公元1229年)平江府检法司检出的法条:“今承法司检具条令:律: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徙一年半,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苗子归官主(下条苗子准此);律:诸妄讼公私田,若盗贸卖者,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徙二年;敕:诸盗耕种及贸易官田(泥田、沙田、逃田、退复田,同官荒田,虽不籍系亦是),各论如律,冒占官宅者,计所赁坐赃论罪,止杖一百(盗耕种官荒田沙田罪止准此),并许人告;令:诸盗耕种及贸易官田(泥田、沙田、逃田、退复田同),若冒占官宅,欺隐税租赁值者,并追理。积年虽多,至十年止。(贫乏不能全纳者,每年理二分),自首者免。虽应召人租赁,仍给首者。格:诸色人告获盗耕种及贸易官田者(泥田、沙田、逃田、退复田同)准价给五分。令:诸应备偿,而无应受之人者,理没官。[46]
这是目前能见到的宋代最为完整的一段检法司检出的法条,足见若无完备的档案架阁制度,地方州县检法官员是绝无可能一一检出如此详备之法条的。
四、结论:唐宋司法职业化倾向的出现,预示着国家治理方略的转变,是唐宋司法公正及政治清明的重要条件
现代法学理论认为:法律家的职业威信是国家规范效力的可靠保证,法律家的职业自治则是司法正义及现代社会公正的基本前提。严格说来,古典中国在儒家意识形态占主导价值的文化形态中,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法学家与司法职业化,为何宋代社会单单出现了司法职业化之趋向?这是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我认为欲解答此一问题,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社会变革下,治国方略的转变。即由对立法的重视转向了宋于五代之乱后大规模的司法改革。唐于中前期曾颁布了一部享誉世界的法典——《唐律疏议》。据此,说到中国古代法治的辉煌,人们便不得不提及这部于中外古今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法典。其实,这对宋代来说,并非十分公允。因为宋代司法的成就很容易湮没在唐律法制成就的夺目光环中。其实,与唐相比,宋的最大成就不是立法上《宋刑统》的颁布与《庆元条法事类》的制定,而是宋初以来大规模的司法改革。举其荦荦大端者有三:一是以读书人,即士子充当地方各级司法官员,以取代五代以来的马步牙校恣意司法的局面;二是重视法律考试与法律教育,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宋代的法律考试规模空前,种类逾唐,法学教育重视法官人格的培养,颇具时代特色;三是法官的选拔有其严格的条件与程序,州级司法及中央三大司法机关中出现了一批具有职业化特色的司法群体,其专业化程度走在世界司法文明的前列,司法公正成为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
其次是最高统治者司法理念的变化。宋代的统治者惩五代十国战乱之弊,司法理念与前世朝代相比,变得的更加务实,他们不再空喊民本及仁政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地的把儒家的这些理念落实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太祖、太宗于建国伊始,便派监察御史分巡诸道,并在一定程度上行使司法审判权力,这是战乱之际纠弊的重大举措。同时,宋太宗又置“审刑院”于禁中,把司法公正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太宗常说:“庶政之中,狱讼为切。”北宋末至南宋初,随着政权的南迁及江南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利益多元化的呈现,宋代政府又把司法治理的重点转向了“民事”,为政以“民事为急”。
最后,宋代司法职业化趋向之出现还与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觉醒及老百姓生活的诉求密切相关。余英时先生曾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把宋代士大夫的主题意识概括为“以文化主体自居”、,以“政治主体自觉”、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与担当精神。[47]余先生认为,宋代之士人与唐代士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由贵族走向了庶民。其实,宋代士人作为法官的主体,通过法律考试与科举考试走进了司法职业队伍,他们的文化自觉精神与政治自觉意识反映在司法与实务上就是职业化趋向的出现。这种职业化趋向除了表现在司法程序上的“鞫谳分司”外,还集中反映为宋代郑克《折狱龟鉴》,乃至宋慈世界上最早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的问世。
再就百姓的生活诉求而言,宋与唐中期之前的朝代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及土地私有制的深入发展,婚姻、,田宅、债务之类的诉讼已成为百姓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儒家的“息讼”观念虽还经常在士大夫的判词中出现,但那不过是法官教育当事人的说词而已。诉讼当事人的权益之争早已代替了那些空洞的道德训条,务实的法律判决是宋代判词的时代风貌。百姓对司法的职业化诉求已是人们过日子的规则与逻辑,也是宋以后明清市井文化的常态,这从其后的三言二拍及章回小说《水浒》的描写中,也可略见一斑。
如果说,现代的司法职业化,是指法官群体或法律职业群体的自治与独立的话,那么宋代还不可能有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职业化群体。但若不是以此凝固化的概念简单地裁定历史,不是以现代人的傲慢眼光蔑视传统,我们就会发现自唐至宋,确实出现司法文明史上少见的司法职业化趋向。所谓“趋向”就是一种典型形态出现之前的“萌芽”或“状态”,对这种“萌芽”或“状态”给予挖掘并进行适当的解释,既是法史学者的职责,也是一个法史研究者对中国司法传统及司法文明史进行现代叙事的一种新尝试。
傅斯年先生曾说: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同异而立论,则唐宋有殊别。唐宋社会变革既是一种事实上的历史突破,也是学界一直关注的一个大课题。然而,以法史的眼光,从唐宋之际司法职业化之趋势的角度观察此社会变革,并把它与国家治理的方略相关联,这在学界还是首次。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是在中国社会发生变革的时代,国家的治乱兴衰往往与法律的治理模式互为表里。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以至于秦汉,国家的治理模式走过了由巫治到礼治再到官僚之治的模式,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治理模式也由贵族礼制走向了官僚法制。[48]就其历史进程而言,原生态的生长于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中的官僚型法制,尽管其身上自始至终都套着两种沉重的历史枷锁,即宗法礼制与皇权专制的束缚,但在它的内在机制里却依然顽强地生长着官僚理性与法制理性。
所谓官僚理性,是说古典中国自战国以来,尤其是秦统一中国后,官僚机器就格外的发达,其中的设官分职制度与官员考课制度,不仅强调“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而且还对官员的责任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其中既有经济责任,也有行政责任,更有刑事责任,古代中国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故乡。所谓法制理性,既表现为古典的“罪刑法定主义”之萌芽,如刘颂倡导的“律法断罪皆得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49],也表现为唐宋之际,州县之地方,尤其是州级司法的职业化趋向之出现。
就司法的专业性而言,尽管唐宋时期地方之长官,如知州、知县等,仍然是行政兼理司法,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所谓的司法行政不分,更不要以为唐宋州县司法与汉唐及后期的明清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唐宋州县,尤其是宋代州级司法,不仅长官要亲审囚徒,而且长官的判决主要是建立在州级属官——即州县幕职官员的拟判上,宋之州级属官中的司法参军的主要职责就是“检法议刑”,这是宋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最大特色。检法官员的设置及检法职责的专业化,既是宋朝政府应对唐宋以来社会变化、诉讼增多、百姓渴望司法公平、政治清明的重大举措,也是宋王朝总结唐中期之后及五代十国以来“司法黑暗,刑罚残酷”之惨痛教训,而采取的治国方略之转变的重大措施。
司法的专业化与侦、审、判的分工制衡化,虽不能完全保证整个宋代司法的公正,但任何时代的司法公正都离不开这两个条件的支撑,而司法公正又是古典中国政治清明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司法不仅关涉每一个人的生活、财产及自由,而且还与人之生命及尊严密切相关,司法公正则社会安定,生活和谐。司法不公,则老百姓怨声载道,社会矛盾突出,乃至“逼上梁山”,揭竿而起,故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与政治清明息息相关。
就宋代的州级司法而言,检法官专门职责的设置及“鞫谳分司”的权力制衡是宋代司法公正与司法职业化的内在条件;而“架阁库”制度与民事审判“给断由”的制度,则从外部给予支撑。“千文架阁法”的施行保证了检法官“检法议刑”职责的行使,“给断由”则要求法官必须通晓法律,熟谙法理。内外因素结合,上下制衡相维,使得唐宋州县的治理于中国司法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正如时人所言:“本朝比之前世,刑狱号为平者,盖其并建官师,防闲考核,有此具也”。[50]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年01期 (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