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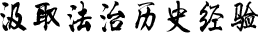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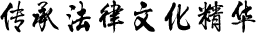
2018年11月24日晚,名家讲坛暨洪范学术论坛第85期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沈家本堂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注释律学中的‘六杀’与‘七杀’”,主讲人为吉林大学刘晓林教授,与谈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徐立志教授和西北政法大学陈玺教授。本次讲座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春杨教授主持,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景良教授、李栋教授、蒋楠楠老师以及众多法科学子参加了本次讲座。

刘晓林教授在讲座
讲座伊始,刘晓林教授指出,“六杀”与“七杀”是针对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大量杀人行为所做的类型化的概括。作为一种“定型化了的典型”,较之刑事法律规范体系内的其他“罪名”更具有抽象性、概括性。“三父”、“八母”、“五流”、“六赃”、“八议”、“十恶”等大量此类表述体现出传统刑律及注释律学的上述特质。其后,刘晓林教授就“六杀”与“七杀”的提出、性质、内容及其分歧三方面进行了系统讲授。
关于“六杀”与“七杀”的提出,刘晓林教授指出“六杀”与“七杀”之说主要见于律学著作、现代辞书与中国法制史教材当中,不同出处所论及之内容的表述与侧重各有不同。从时间顺序看,可见其中沿袭痕迹以及沿袭过程中针对具体内容的认识所产生的偏差。传统律学著作中基本呈现“六杀”与“七杀”二说并存局面;现代辞书中二说出现撕裂,论者多将其限定为唐律之概念划分;而中国法制史教材中几乎一致采“六杀”说而忽略“七杀”说。
基于对唐律、明律、清律等法典的观察,刘晓林教授认为,“六杀”、“七杀”的性质与“六赃”不同——“六赃”直接就是法律规定,而“六杀”、“七杀”并不载于法律文本,而只是学理解释。他还指出,注释律学中“六杀”与“七杀”的概括是对杀人犯罪行为的类型化概括,其划分标准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具体来说即相对于犯罪行为本身而言的预谋内容、预谋程度与罪过形式。
关于“六杀”与“七杀”的内容及其分歧,刘晓林教授指出“七杀”的具体内容包含“六杀”,二说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应将擅杀、殴杀、劫杀等内容纳入杀人罪类型化的概括当中。依据律学考证与其司法实践经验分析,他认为,秦汉时期的擅杀应当是贼杀的特殊形式,唐律中的擅杀、贼杀等相关杀人行为皆作为故杀来处罚,不应与谋杀、故杀等术语并列;斗殴杀实质上是斗杀的不同表述,“斗”与“殴”仅是同一伤害行为的不同阶段,殴杀不应与谋杀、斗杀等术语并列;至于劫杀,宋元明清律学著作中皆有纳入“七杀”的观点,现代辞书中采信者亦不鲜见。
在总结中,刘晓林教授认为,“六杀”与“七杀”本质上并非立法语言,二说只是传统律学著作中针对法律规范内容所作的学理解释,其类型化划分标准是具体杀人行为的主观心态。所见之律学著作中,“七杀”之说盛于“六杀”,但二说长期并存;现代辞书中二说的注解内容开始出现矛盾;中国法制史教材全盘采用“六杀”说,进一步走偏。将“六杀”与“七杀”的具体内容作比照分析,可以较清晰看到:谋杀、故杀、劫杀、斗杀、戏杀、误杀、过失杀是传统注释律学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概念,是律学家对于纷繁复杂的杀人犯罪行为高度抽象的概括与总结,是“定型化了的典型”,此说不仅是针对唐律立法内容所作的较为全面的概括,也对后世立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讲演结束后,讲座进入了互动环节。徐立志教授表示,刘晓林教授的论证改变了多年来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仅根据“六杀”与“七杀”在法典中未出现就断定“六杀”与“七杀”并非立法语言,似失于武断;若能结合例来进一步分析,将更具说服力,如清代《理藩院则例》等等。此外,徐立志教授指出,本次讲座具备非常强的法史研究方法论意义:第一,法史研究应该进入精致化研究阶段;第二,探本究源的探索精神值得提倡;第三,将律学与律典研究有机结合才能把问题弄清楚。

徐立志教授发言
陈玺教授从法律演进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还从法律史研究路径与学科定位角度出发,陈述了意见:第一,法史研究要结合法律条文本身,法律条文又须与法律实践相结合;第二,律学研究应具有比较视野。
陈玺教授 发言
发言
本校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巩哲向刘晓林教授提问道,著作编纂的不同目的是否影响了“六杀”与“七杀”的表达。刘教授回答道,影响是有的,但直接原因还是由于先入为主、沿用前说,未必与编纂体例有关系,否则应该有两说的基本辨析。
本校法律史博士研究生王蓉向刘晓林教授提问道,清代“斗杀”之规定较历代规定是否有突出变化?变化在哪?刘教授回答道,变化非常明显,主要从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时期开始。“斗杀”从产生之日起,立法者就困惑于如何将其与“故杀”相区别。清代以前,主要是在立法上设立二者的区分标准,而清代立法则是在这两种罪名的内容中增加细节方面的规定来将二者加以区分,看似进一步精确化了区分标准,但现实案例中,二者相似之处甚多,精确二者在构成要件上的规定反而更模糊了两种罪名的区别。
陈景良 教授进行总结
教授进行总结
最后,陈景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第一,关于实证与贯通的关系,他指出:治学须从实证入手,无考据不得为史学;思考须从全局着眼,没有贯通不足以成学问。第二,若选择做法律史的非主流研究,即研究一些边缘问题,那就一定得从新材料、新方法或新视角入手;否则法律史研究选题着重点应该从主流入手,要回到法律规范及其适用上,司法、诉讼是法律史研究的主流方向。第三,规范、法典、司法实践三者相结合,才能做出很好的学问。第四点,应该回归法典本身探寻立法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法理。法律史的研究必须将文献和部门法理论结合起来。
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人蔡森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