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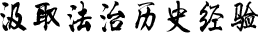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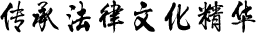
【中文关键词】 法;正当性;儒家;道家
【摘要】 《韩非子》为回应当时政治所面临的困境,主张以法为治。以有别于儒道两家对政治秩序的理解,同时又继承了儒家实现公正社会的关怀和道家因循的行为方式,来阐释法治的思想基础及其正当性。谋求以“法”作为惟一的规范形式,并将正当性建立在公义和政府的权威之上,以最终颠覆传统规范“礼”的神圣性基础,根据其独特的人性论和历史观,延续商鞅的治理方式,放弃儒家对于善良政治的追求,以法代替礼,构建以君主为最高权威的新型政治秩序。《韩非子》的法治,意味着将政治秩序建立在具有确定性、系统性和消除任意性的规则基础上。然而,将法的正当性建立在权力之上,摆脱既有的所有权威系统的约束,则存在以暴力进行恐怖统治的危险。
【全文】
引言
中国历代王朝,除秦以外,多以“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为其宗旨,皆不明示以法为治,并因暴秦采纳法家理论之故,法家之声名,长久以来在先秦诸子中,陪诸末流,甚而有阳儒阴法之说。然自近代以来,西学以法治声威,挟船坚利炮,践临东土,使国人再不敢蔑视法治之力量。于是,法家研究,一时也成为了沟通中西方法学的桥梁。甚而有学者指出法家理论乃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瑰宝,弘扬此传统正为中国现代化之助力,破除中国古代封建统治残余,接纳西方法治思想,所不可或缺{1}。亦有学人将法家理论与中国专制统治相联系,以剖析法家理论来声讨中国的专制统治{2}。亦有很多学人已经指出此法治非彼法治,中西法治观念,从法家理论的意义上,势成凿枘{3}。然而,法家之法的理论,无论背暴秦之名,还是负瑰宝之意,究为现代政治之思想助力,抑或中国接纳西方法治思想,实现现代治理的障碍,皆不可不辩。
辩,则需着力点。言之整个法家理论,则嫌宏阔,非小文所可为功。选诸一子,尽力疏释剖判,或可以一斑而窥全豹。韩非子向以集法家之大成而著称,若欲明晰法家之法为何物,理解韩非子所言之法,当为不误之选。韩非子之法,虽未必当得法家之法的全部,但揭示法家之法的精髓,应为不诬。然而,韩非子所著为论,载之于《韩非子》一书。但《韩非子》一书未必全是韩非子之论,为免于介入力所不逮之文本考证,本文特以《韩非子》名题,其根本意在从其本文理解疏释韩非子之所谓法。
众所周知,韩非子受教于荀卿,却以倡法名世。为什么他批判了儒家素来主张的礼乐道德仁义,而独倡导以法为治?他的法又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而且应该代替礼乐道德仁义而为治?他的法治希望构建怎样的政治秩序?人们在此种政治秩序中将过上怎样的生活?而他以法为治的基础又何在?这些问题,前人或多或少也有所涉及,但是,若欲深入理解韩非子的法治理论,则除非仔细阅读和理解他的论述,不能竟其全功。故,本文仅欲以上述诸问题为其线索,对《韩非子》加以最通常的理解。或可与诸贤一辩,以窥其法的堂奥。
一、为什么是法?
(一)以儒家立场与儒家辩论
韩非子不是现代的法学家,《韩非子》也不是一部法理学著作。他没有想到要解决法是什么的问题,尽管在他的思想中呈现出了法的面貌,其中也有与现代法律观念相通之处。然而,我们必须明确,他只是希望或认为法能够回应他所观察到的混乱的政治秩序。这不能不让人发生疑问,韩非子受教于荀子之门,无一语言及礼,却毫不犹豫地扛起了荀子的另一面大旗--法。当然,也可能他之主张法治,而不是礼治,与其他的思想有关,但是,我们依然不得不面对荀子的礼法理论对他的影响。
从这一点而言,我们知道,对于儒家来说,韩非子的思想具有着相当的革命性,然而,他所欲解决的问题,却基本没有超出儒家所关注的领域,此种革命性,只是发生在方式和方向上。如果我们把韩非子放弃礼,而选择了法,看做是一种颠覆的话,他也只颠覆了儒家的方式,却并没有颠覆儒家的关怀。我们只要略微阅读一下《韩非子》的文本,即可知道他对儒家所提出的挑战,无处不在。为什么呢?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不同意儒家对人类及其人类社会的观察以及期待。孟子见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指出了君主以利益为其施政导向的危险,而申述倡导实施仁政王道,以使人类摆脱互相劫夺和工具化的命运,指出了政治是使人类免于陷于恶的深渊,而长养其善行的目的,此乃政治为政治,王之为王的本义。无论君主还是普通士庶人等,生活在政治社会当中,谋共同的生活之道,其根本的意义不在,陷溺于利益争夺之中,而是以此人类的团体谋得物质性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超拔自己的物欲和权力欲望,以实现其为人的价值,过正当的人的生活或良善的生活--义。此种理论则奠定在他的人皆有善端的性善论之上。
即便持性恶论观点的荀子,依然主张王道乃政治的正途,亦即谋得人的正当生活。恰恰因为人性本恶,则需要礼法之约束,遏制人趋恶的倾向,使之向善,其政治的目的依然指向人类善良的表现。从一定程度上,儒家的此种政治理念,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恰有相同之处,而儒家的解释学传统中所追述的尧舜禹汤文武,无非是此一政治哲学传统的符号化表达,也可能是抽去了具体历史事实的符号化表达,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此政治哲学与中国历史事实便作了有效的切割。然而,韩非子对于此种理论则大不以为然,这就是我们能够在《韩非子》中看到,大量的有关此一符号系统的别样阐述的原因。尽管他也承认孟子对于政治现实的观察,也承认荀子对于人性恶的挞伐,然而,他却不认同他们的解释,同时也不认同他们主张的治理方式--仁政与王道。在一定程度上,韩非子通过重新阐述历史和人性,来阐发他全新的政治追求,而法恰恰是其中一关键的方式。
因而,在他看来,儒家所强调的仁政与王道,或谋求人类良善的生活,根本不是人类政治生活所实现追求的目标。在根本上,是儒家学者不能直面人类生活的事实状态,而产生的一种虚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利害关系,这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在人与人之间,试图构建良善关系,或者说引发和鼓励人类的善良意志或善良行为,是对人的此种利害关系的错误认知所致。因而,对于政治社会而言,对此无需改变,甚至也是无法改变的,只是需要清楚地知道和利用这样一种关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以免自己成为被虏获的对象。
职是之故,韩非子似乎拒绝了孟荀的政治解决方案,事实上,他却一直沿着孟荀的思考方式,甚至一直沿用他们的主要概念--心、性、情。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整个理论依然奠定在儒家理论的基础之上。之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突破利害关系,因为人人“皆挟自为心也”。即便是父母子女,也不离利害相怨:“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而君主大臣之间,形势更行险恶。“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韩非子•爱臣》。这种观察已几乎与孟子的无二无别。只是孟子认为这种现象,乃人类的不良现象,非是人类社会所当有的,但韩非子则认为这本属人之常情。“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奸劫弑臣》)。“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韩非子•二柄》”,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利害关系,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人,或者说,这就是他所认识的人性,这是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或者说人类治理中的前提。因而,人们因为具有此种性情,所以,可以说人人都生活在极度复杂和危险的情境中,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需要随时防范他人,这在《韩非子》“八经”、“六反”、“孤愤”甚至“说难”中,都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对此,不同于他的老师荀子,他并不认为这是人性恶,在他看来,只是事实。因而,以礼义教化的方式,“化性起伪”,以实现王道政治,使得政治社会当中获得正义,期待人类都过上善良的生活,为韩非子所不取。政治的根本问题,不是实现王道仁政,而是如何基于此种人情,而整顿出一种政治秩序,不使此种人情利害,成为紊乱秩序的因素。
所以,可以说,韩非子似儒家一般,关注公共秩序,他的全部理论努力,都不外乎要造就公共秩序,然而,他却既消解了儒家善良政治的目标,也抽离了儒家政治目标赖以存在的人性基础,无论人性善恶,都可成为顺之而行或逆之而成的善良秩序的基础。韩非子却恰恰认为人性受制于利害,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而公共秩序的实现,必须以此为根据,别无他法。
(二)以道家情怀导引治理方式
我们不能忘记《史记》中,司马迁将韩非子的传记与老子合在一起,这固然有司马迁对韩非子思想的理解,然而,却在另一方面说明了,韩非子除出自于儒家门墙,可能更带有强烈的道家色彩。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韩非子以“解老”、“喻老”为题,解释老子的《道德经》。正因如此,这就给他观察和解决人类的政治问题,提供了有别于儒家思想的资源和方式。故,他不认为政治社会的治理,应该像荀子那样,逆着人性而行,而应该顺应人的这种“皆有自为心”的本性。所以,他说“凡治天下,因人之情”。逆人之情,则无法达到治理的目的,也无法建构合适的政治秩序。因而,政治治理应该另觅方式和方向。
既然人人皆挟自为心,无可厚非,不必施设制度扭转,也无可扭转,同时人本无性善,所以,自不必将人类社会的治理和人类趋向于善良,当做目标。因而,韩非子的革命性,在于他重新调整了人类生存和治理的条件,那也就是说,韩非子所谋求的政治秩序,是基于他所认识的人类的生存现实,是无法加以改变的。因而,人类的政治治理只是谋求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本身并不会以期待人的生活变化和向善为其目标,也不以巩固人们之间的情感、忠孝、信义为其价值目标,只是为谋求共同生活必须具备的秩序而已。换一句话说,他认为他的儒家前辈们,错误地提高了人类政治秩序的目标,错误地认识了人类的心、性和情。因而,整顿政治秩序问题,首先必须放弃他们的政治目标以及方式。而让政治秩序问题重新回到人类生存的事实层面上。从这种意义上说,韩非子试图构建的政治秩序,所实现的目的就是趋利避害,而不是向善。所谓:“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同时,不仅仅人心不可逆,就是世事也是不可逆的。在这里,韩非子似乎在一言未及古老的“易”的观念,便直接将“易”的思想应用到了它对人类历史的观察上。我们不难看出,他在强调因应和顺应人心与世事变化的观点时,显现出的一副非常典型的道家思想的面孔。“不逆天理,不伤性情”,“守成理,因自然”(《韩非子•大体》)。因而,他实际上是以道家的面目批评他的儒家前辈的。“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讘?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阱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韩非子•奸劫弑臣》)。很显然,韩非子对当世横议的儒、墨人物,深得君主器重,却并不了解治乱的根本,而像他这类对治乱兴衰深得体会之士,不被了解,深感失落和遗憾。而这些儒、墨人物之不谙治乱的原因,在于不懂得世事变化,只知独守前辈之教,不通因应变化之道。“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韩非子•五蠹》)。于是,他超越他的前辈,引入了政治秩序的一个新变量--历史,换一句话说,他无意从根本上推翻儒家的仁义和墨家的兼爱,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它们作为政治目标,但是,韩非子认为这些政治目标已经与当前的现实相背离,不再能够实现。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韩非子•五蠹》)。“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所以,当今之世,若欲整顿政治秩序,就必须将其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而不能泥古不化,或将传统的政治目标和方式,奉为圭臬,无论此种目标和方式,多么正当,却因为条件的改变,而无可行之处,只能增加政治的困境和危机,无助于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韩非子•五蠹》)在韩非子看来,当今之世,仍以仁义、兼爱谋得世治,无非如守株待兔般可笑。然而,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究竟韩非子认为是政治秩序不能以仁义兼爱为目标呢?还是不能以仁义兼爱为其治理方式呢?若说只是方式不再适用,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因为人的性情所致,若说是政治目标,那么依照人的性情,上古之世,人的性情则不如当前这般好利恶害?那也就是说,在历史的发展中,人的性情也发生了变化?然而,韩非子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人的性情是否会变化。他接着申述,“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韩非子•五蠹》)
而孟子之徒却仍倡“得民之心”。韩非子以为“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韩非子•显学》)。当今之世或有史以来,绝非如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韩非子看来,此种看法恰恰混淆了政治问题的根本,当今政治秩序的混乱,恰恰典型地颠倒了政治秩序的关键问题,政治秩序的关键在于巩固统治者的威权,此种威权的巩固与否,并不在于民众能否得到重视和尊重,而在于君主本身有无足够的能力和方式,维护其权力。“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先王之治,从其根本而言,也绝非以百姓或民众的利益为指向,如此,则国家的目标和航向,反操控于民众之手,则君主安在?此可谓乱亡之道,绝非致治之途。儒、墨之误,在于盲信人性之善,和政治乃谋人类相亲相爱之道,所谓的仁义兼爱,以为德厚方为政治的根本。从韩非子的观点,此为不明政治之道,也不明人类之性,更不明当务之急。因而,他主张,应该象道家一样顺应当今的形势和困境以及人的性情,重新认识政治秩序的基础性条件,并重新确立新的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从而,他接过商君的改革大旗,喊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的口号。
(三)以人类现实决定政治目标
按照韩非子的看法,当今之世,以先王之道,就是致乱之本。因为,当今天下乱亡,在于人人皆有自为心,既是人人好利恶害,那就除了有利于自己的行为,别无其他的正当可言,因而,对治当今的乱局,不是依靠仁义谋略所可成功,而在于权力的大小--“争于气力”。所以,当今的政治危机,在韩非子看来,不是其他的危机,而是君主的危机,是君主陷入了重重私利的包围之中,却未认识到或无良策对治。因而,他说“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韩非子•孤愤》)。所以,“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群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韩非子•二柄》)。因为,“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韩非子•孤愤》)。当今之世,君主被私利之徒,重重包围,几无可信之人,“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韩非子•守道》),若欲维持有效的政治秩序,其根本在于杜绝人人只谋私利,而绝不顾及公义的现象。然而,君主常被奸人环绕[1],若非有超凡智能,如何能够摆脱近臣操弄?同时,君主亦为常人,若受制于自己的私欲,则很难摆脱巧言的迷惑。所以,所有的政治考量和政治秩序的建立,在这里,从韩非子的论述中,似乎又跳出了对历史变更的顺应,而重新将政治社会的难题普遍化了。所谓“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因而,我们不能期待以尧舜的智慧来进行治理,我们必须要面对人类的现实,“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韩非子•难势》)。因此,要把人类的政治问题,放在一个普通人的层面上,方能把政治秩序的建立,安放在一个合适的基础之上。因为,无论是君主还是普通民众,不过都是常人而已,所以,他们都受制于人的心、性、情,我们既无法依赖也无法超越它们,来建构合理的政治秩序。因而,人类的统治,无法期待依赖圣君贤相的智慧,同时,也无法效法道家的自然之道,无为而治,那只能导致局面更加不可收拾。
因而,政治无法依赖个人来建立秩序,也不能期望通过礼义的教化来建立秩序,必须别寻他途,因为,个人无非谋私而已,既是谋私,礼义怎能够发生作用?若依赖个人为政,君主势必常常为此种私利重人缠绕。所以,“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只有法,才能既破除君主凭其喜好以赏罚,又能避免大臣、近人谄以谋利,一切皆以法度为准,既不恃君主的德行与智慧,又可免大臣以其才能逞私意。“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韩非子•有度》)。
孟子劝诫君主不以私利、足私欲为政治目标,若君主以谋私利、足私欲为政治目标,则难免臣民将其当作实现私利,满足私欲的对象,因而,倡导与民同乐的王道。韩非子认同孟子劝诫的结果,却不同意他解决的方式,他认为,即使君主放弃私利,而行公义,却未必能够避免臣民行私利。因而,他认为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君主要有足够的办法,控制臣下谋私利的冲动,将所有臣民的行动导向公义上来,“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韩非子•饰邪》)。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明于公私之分,明于公私之分,莫若以法,“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韩非子•守道》)。所以,“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因而,在他看来,法之超越了任何治理方式,在于它能控制“自为心”的泛滥,既能防范君主,亦能防范大臣,对君主可防庸主滥权,对大臣可防范私心膨胀。韩非子据此告诫,君主若想有效控制,就只有依靠法治,建立政治秩序,“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法,之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全在于能巩固君主的权力,又能有效地控制人的好利恶害之心。它只区分公私、利害以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而不在于区分善恶、是非、好坏、勇怯,美丑、和乐狂躁,以成就善良的人类生活。法之应该取代仁义、兼爱甚至无为而治,完全是因为韩非子对人性和政治重新认识的结果,其根本在于他否定了以“德”为目标,以“礼”规范的传统政治。因而,政治秩序的重心,在韩非子这里,全然由孟子的民贵,转向了尊君;由孟荀的向善,转向了禁奸去私。
二、什么是法?
(一)绳墨权衡之为标准
《韩非子》认为只有法,才能解决当今的政治危机,从他的观察来看,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说,只有法,才能解决人类的政治问题,其他的方式都无法实现,因为缺乏实现的条件呢?我们知道,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不也是一个坚定的法治论者吗?但是,《韩非子》的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功能呢?到底什么才是他所说的法,而法的正当性又何在?或者换一句话说,法到底如何能够体现的是公义呢?对于韩非子来说,法,之于整顿政治秩序,具有着无上的地位。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名,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韩非子•有度》)。
从这段对法的功能略显夸张的说法可知,他所说的法能够提供种种标准,来衡量各种各样的事物,并且这种种标准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法,在一定意义上讲,与当时把法比作规矩、权衡、绳墨之类的在先说法,没有太多区别{4}(P.336-337)。那也就意味着,它具有某种确定性或恒定性,以摆脱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的操控。同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非有如此诸多标准的存在,就无法创造出合适的事务。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没有法,就没有政治秩序?如果我们用他所批评的一位先贤的话,恰好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墨子•法仪》)
既然规以成圆,矩以成方,治国就需用法,法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抛开人的私意或用现在的概念--意志,在此多变和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心或意志之外,明确以法为标准,作为指导人的行为规范。因为,若没有法,人就会以谋私为务,弃公义于不顾。尽管韩非子没有像荀子那样申述性恶泛滥的后果,然而,很显然,他认为若整个人类私利盛行,那么政治秩序也就荡然无存了。从此看来,他认为法是使人类共同生活得以实现的条件,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人是不是必须保持一种群体的生活,他只是非常强调当今政治的混乱,是因为没有坚持把法当作人类共同生活所必需的标准。是否可以理解为,他把法当做人类社会之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标准,政治之为政治的基本标准?而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能够有某种力量提供一种实现公义的标准?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人心,无法依赖仁义、兼爱、德政来实现政治秩序,然而,我们又必须建立某种秩序,以超越于任何人私意的法,来给出公共的生活或政治规范,就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并且,这个选择可能不必一定局限于当时的政治情境。那么,后人经常指出韩非子的法治,只图救世之急,是不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呢?[2]
所以,他反反复复很多次表达了法的功能之一就是废私。“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诡使》)。“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长短,王尔不能半中”(《韩非子•用人》),这就更加明了了韩非子的意思,此法的重要性,并非是人所可代替的,即使是如圣王尧,也不能弃法不用而得国治。那么,他屡屡重述的圣王故事,反对的不是法治,是什么呢?更进一步的说,治理国家和维护合适的政治秩序,不在于你劳心费力,而在于能否因循自然,“是以圣人处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第二章)。他说,“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若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他的法治,在这个意义上,就具有了浓厚的道家色彩。或者,可以说正是道家“无为”在政治上的应用,也有儒家赞赏的“垂拱而治”的意味?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之坚持法治,在于排除私人意志和欲望于政治之内,不仅仅要排除被统治者的私人意志和欲望,同时也要排除统治者的私人意志和欲望,如此,方能真正建立一个具有相当确定性的行为规范,因此,一个稳定有效的政治秩序,方可以期待。
(二)统一性保证确定性
法除了确定性外,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统一性,所谓“一民之轨,莫如法”,“法莫如一而固,使民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利矣”(《韩非子•五蠹》)。无论什么人,其行为的是非赏罚,法是惟一应该适用的标准。而统一性的维护,又依赖于它的确定性,他所讲的弥子瑕的故事,很显然就是告诫君主不能以私意侵入法的执行,然而,这也是人类所面对的根本困境之一。即使韩非子提出了如此严厉的法治理论,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也力有未逮。他的法治理论之效果大打折扣,也是他的根本观察,中人之主如何摆脱自己的权力欲的恣意呢?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我们不能说,韩非子对于人类受控于“自为心”和“利害计较”,毫不关心。他所主张的法治,无论如何都带有一种将人从此种自为和计较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意味,尽管他认为这是无可改变的,但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不应该加以约束和控制。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不是儒家思想的别样延续呢?
同时,《韩非子》中似乎从来没有表露过,既然人人皆挟自为心,那么,这些私利具有其正当性,应该受到一定范围的保护,就像荀子所表述的那样:“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但是,他关注的方式,不是从普通人角度出发,而是从君主的角度出发。因而,人们求其私欲的实现,势必就是制造政治混乱的源头,不应是保护的对象,却是规制和控制的对象。尽管角度不同,并不意味着私利完全铲除。只是他特别注重秩序的形成与维护,希望能依法的方式,将所有人的职责和功能确定下来,职责和地位之间没有丝毫的模糊性,使得每个人都能清楚明了自己的行动范围,并以此严格执行。我想,这从他所讲的韩昭侯杀典冠的故事中[3],大致可以推测他为什么强调“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韩非子•说疑》)。那也就是说,他所说的法,主要的功能是,政治社会中不同的人被安置在不同的位置上,通过法的确定,排除所有的个人意志的扰乱,从而构成一种政治秩序的结构或网络,每个人因此在其中根据规则谋取自己的利益,以度过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个结构中生存,同时又必须符合这个结构中的标准--法,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避免危害,连普通看上去对于他人有益,而超越其行动规范的典冠,都要承担行动的后果。对于君主而言,除了以法的方式严格约束臣下,别无其他方法来巩固政治秩序,因为,臣下的守法与否,是对君主或说国家政治秩序,至关重要的。因此才说“官之所以师也”。因而,韩非子的法,在相当意义上,就形成了一种政治生活中的系统性标准{4}(P.351)。任何人都不应该脱离这个系统而获得利益,必须成为这个结构中的一部分,只有发挥了你在其中的作用,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所有人都应该成为法所控制的对象,而没有所谓的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行动的余地。但是,人人皆有自为心,禁绝和控制人心的自由行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才会告诫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
基于上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韩非子之所以如此看重法治,在于他将法当做能够形成有效政治秩序的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性的标准。同时,还应该是惟一的标准。所谓“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韩非子•定法》)。到此,韩非子才揭晓了法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法不是来自上天,也不是由人的内心的善良外化为行为规范,所谓“礼自中出,而非外铄”,它并不体现人类自然的生活方式,也不是来自祖先遗留下来的习俗,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它就是由官府正式公布的成文的制定法。因为只有成文,才能保持其确定性,其制定者必须保证在官府手上,换一句话说,是操控在君主手上,才能确保其统一性。
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年外,虽有难行,不以显焉,故民无以私名。设法度以齐民,信赏罚以尽民能,明诽誉以劝沮。名号、赏罚、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此之谓有道之国也(《韩非子•八经》)。
(三)惟一性保证权威性
所以,法必须拥有最高的权威性,因此,也必须消除社会上种种能够与法竞争的规范,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韩非子》一书无一言及于礼,却抨击“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并且鄙视“不令之民”“恍惚之言”(《韩非子•忠孝》),屡屡批评君主放弃法,而把那些无益于治的人引为座上宾,是颠倒之举。实际上,他就是在消解其他规范在人们心中既有的权威性,为了使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就必须消除其他规范,甚至于不惜宣告其违法。因而才会有所谓的“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以前固有的所有的规范,无论其在原来的意义上,具有怎样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只要与当今的法不相合的,都是非法的,并且要严加取缔。不如此,则无法巩固君主的权威性,无法确保法的执行,也就无法保证稳定的政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凸显: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君主或国家才是最高权威,它所给出的规范和行动标准,具有至高无上性和排他性。同时,作为规范的法,只具有世俗的或权力的根基,别无也无需其他的神圣的正当性来源。从这层意义来看,韩非子试图以法的理论,彻底颠覆一种政治传统,将君主彻底从所有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变成最高权威,而法的权威性,就只是君主或国家权威性的呈现而已。
然而,法为什么应该高于其他的社会规范呢?这在韩非子看来,似乎不是一个需要关心的问题,只需要运用权力消除其他规范,利用人的好利恶害之心,强力推行法治即可。因此,他似乎无需提供一种可期待的生活方式,来证明法的正当性。他只是不断表达,法必须成为人们惟一的行为规范,因为它是有效的,它可以解决政治的混乱局面。虽然他无意特别阐释法的正当性或应该替代其他规范类型的理由,却直接申明它的有效性必须符合民心。所谓符合民心,就是能够以赏罚的方式,来控制人们的行为。但是,“君臣,以计合”,君民不同利,法既是约束人的私心之举,又如何能保证“必于民心”呢?惟一可保证的是,以赏罚为其手段,诱之以利,恐之以害,“虽拂于民心,立其治”。最终,就只能以恐怖的方式出现。
因而,韩非子的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对儒家的一种颠覆。孔子强调政治的丰富性在于,他不仅要维护一个政治秩序,而且还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不仅要人人遵守政治规范,就是韩非子所强调的法,而且还要人人尊“礼”而获得美德和尊严,所以,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不仅仅君主或国家应该具有权威,而且这种权威的获得或保有,应该有其神圣的源泉,所谓“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而且,人们还因为遵循“礼”,而成为有德之人或过上善良生活。政治社会之于人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人成其为人。“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政治学考察高尚(高贵)与公正的行为”{5}(P.6-7)。然而,在韩非子看来,政治根本没有什么使人成其为人的目的,治乱兴衰只取决于君主或国家能否控制人们的行为。而除了法以外,没有任何规范,能够实现此种功能。如果说,西方近现代强调实证法或国家的主权,是向传统的神法和自然法以及教会抢夺权威{6}(P.299-307),那么,韩非子的法,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向传统的天命、德治、民本的政治传统,争夺权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法也颠覆了“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政治传统。
(四)公义的瑕疵及其复杂性
当然,韩非子也不是完全没有提供法应该具有正当性的理由,如他把法当作实现公义最佳的工具,甚至法就是公义的体现。这恐怕就是他的法的正当性所在。然而,什么是韩非子眼中的公义呢?他实际上没有从正面论述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理解他的含义。我们从他的几个表述来分析,大致可能明了他的公义。“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韩非子•五蠹》),“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故明主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韩非子•八经》)。“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韩非子•五蠹》),“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韩非子•饰邪》)。从上述的几种说法,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人人自利,所以,君臣之间的利益是不同的,臣自然会指向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有悖于君的利益,君的利益在国,而臣的利益在家,所以,国、家异利,而臣则谋私而背公。所以,法就是防止臣下谋私,以张公义的规范。从此可以看出,韩非子是将君与国同等看待的,而且,在他看来,只有君主本人才会关注国的利益。从另外一面来看,韩非子的法正当性,不仅体现在对于臣下谋私的控制,同时,也指向君主本人应该放弃个人的私智和私欲,来守护法的公义。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法则具有客观化的意义,很难不敬佩韩非子对人类困境的认识,以及此种治理方式的高明之处。
然而,对于法是公义的体现,依然存在着令人困惑之处,为什么君主的利益就能和国家的利益同一呢?君主与臣民的利益不同,臣民会尽力谋私,君主就不会尽力谋私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臣民所谋取的是私利,而君主所谋取的就是公义了呢?如果不能做肯定的回答,那就意味着,根据法,臣民被迫放弃了私利,去谋取君主的私利,只是君主的私利,顶着国的公义出现而已。事实上,这国的公义,并不代表臣民所需要的私利。但是,问题似乎也没有那么简单,君主本身拥有一国,一国之利都归属于自己,那就意味着亏国以自利,是只有愚人才会去做的。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即使君主治理一国,谋取的是私利,但是这种私利难道真的完全会放弃臣民私人的利益吗?如果我们想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的“牧羊人难道会只顾自己的利益,绝对不顾及羊群的利益吗?”{7}(P.28)就知道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但是,若进一步思考,法既然没有所谓神的来源,也不是历经长久沉淀的习俗,而是由人为创造的规范,人本身又都是自利的,无论是谁来创造法律,又如何来确保其体现的是公义呢?
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怎样批评韩非子的法,都不得不承认,建立人类社会的政治秩序,需要具有摆脱主观性的确定标准,政治秩序也应该建立在系统化的规则基础上,以消除人的意志的任意干扰。然而,这种规则体系是否应该摆脱既有的所有权威系统,而将政治权力当作惟一的权威来供奉,政治权力本身是否会藉着法律的力量,凭借暴力进行恐怖统治,是值得人类思索的问题。而什么力量能够支撑人类,凭借自身的智力和理性或意志,而抛弃过去传统的习俗即“先王之道”,就一定能获得良善的生活?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韩非子所看到的人人“皆挟自为心”是个现实的状况,但是,是不是说这就是人类不可改变的本性,是无可提升或加以改善可能的呢?因而,建构人类的政治秩序,就应该放弃使人过上人的生活或曰善良生活的努力,而只应该成为在法的驱策下苟延残喘,甚或只有实现君主或国家目的的工具价值?
尽管儒家或久远以来的一种政治传统,已然无力应对政治危机,是不是人类对政治生活就不应该再保持美好的期待?如果说我们生而为人,在政治社会当中,都能谋求过上高贵(君子)的生活,是很难实现的目标,但是,一种政治秩序留给人们追求此种生活的自由,总应该留有足够的空间,甚至应该是值得崇尚的。尽管韩非子之强调法,更倾向于道家的因循之道,但事实上,他背弃了道家而继承更多商鞅控制的技艺,在一定意义上,法成为了控制人的行为甚至人心的技艺。将其惟一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其他生活的空间和可能性,所以,后人视其法治为专制,也是不无道理的。然而,若说他的法治,只是为了专制统治,那就忽视了人类的复杂性,就连孔子也无法否认“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只是说若以此为政治的全部方式和目标,那就低估了人类的品质和能力,以及贬低了人类共同生活的意义。
表面上看来,韩非子法的理论针对的只是当时特殊的政治危机,甚至于他对法的正当性的争论,还存在着诸多疑问和困惑,无法令我们满意,但是,他对于治理方式的寻求和政治秩序存在条件的解释,都恐怕不是能够随着那个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消逝而消失的。我们今天所寻求的法治,尽管与韩非子的法治有着相当的差别,但是,他所提出的治理困境,难道不是我们所面临的吗?
(责任编辑 王人博)
【注释】 作者简介:孔庆平,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在《韩非子》里的“爱臣”、“八奸”、“备内”等篇章中,多有论列。
[2]太田方在其所注的《韩非子翼毳》的序中,即指韩非子的思想无非救世之急,非人类政治所常务。请参见[日]太田方:《韩非子翼毳》,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2页。
[3]昔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悦。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
【参考文献】 {1}王邦雄:《韩非子的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7年版。
{2}熊十力:《韩非子评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3}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思想史》,秦传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8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