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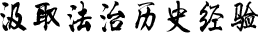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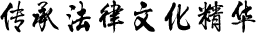
内容提要:
在土地私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宋代,利益的多元化孕育并发展出了形形色色的私有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不争事实。宋代私有财产权中的“个人”不同于西方,是家庭之私与“伦理个人之私”,还有“外商个人之私”。私有制上升为权利须经法律认可与司法保障。在没有民法典及私法观念的历史条件下,宋代法律通过经义、敕令、律典、令典诸方式规制人们的民事生活,又通过司法保障各种类型的私人财产权利。这种保护既适用于普通民众,也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济。其彰显的时代特色风格独具。
关 键 词:
私有财产权/宋刑统/砧基簿
标题注释:
本文系汪世荣主持的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治文化的传统资源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项目号14ZDC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就学术史的回顾而言,学界以往对宋代私有财产权的研讨主要是以现代部门法之理论,对宋代的财产权利做了物权、债权、财产继承权之划分。①近年来,深入而且又有新贡献的代表性成果是柳立言、戴建国以及程民生三位先生的论著。柳先生的最主要贡献是:(1)率先指出了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正月乙未的诏书,是宋代“同居共财”制的首要变化,这个诏令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成人男女“白手起家”所赚得的财产属于个人所有;(2)鲜明地提出了宋代法律呈现出了“中产之家”的特色,局部打破了“同居共财”的儒家传统。②戴建国则从宋代的田宅“典权”入手,指出影响明清两代数百年的“一田两主”制,皆发端于两宋而独具时代特色。③程民生则指出:宋代法律对公私财产的保护具有同等法律地位。④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宋代私有财产权的历史事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然而,由于以保护个人权益为主旨的现代权利观念是从西方传来,而非中国古典文化所固有,这就为学界研究此一问题带来不少困难。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儒家语境下私有财产权中的“个人”是何种意义上的“个人”?其次,私有制若上升为权利,必须得经过法律这一中间环节。宋代没有民法典,也没有私法观念,且刑法典是以惩治犯罪为重点,它该如何保护私有财产权呢?最后,即便宋代存在立法与司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已成过往,非人们现在能直觉感知,这就需要论证。论证能否成立,既要取决于文献材料又需要论证方法的有效性。笔者的基本理论预设是:一个社会,若法律与司法能保障弱势群体中个体的正当私有利益,则私有财产权的普遍保障必成为共识与历史事实。
以上这些问题必然困惑着我们,也给笔者试图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探索的勇气与动力。
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⑤
1.儒家语境下,宋代有无私有财产权?若有,内容为何,法律怎样保护,其特征与历史地位如何?
2.何种意义的私有?西方法学理论解释中国私有财产权的意义与局限是什么?
一、宋代私有权的历史事实与分类
私有制是私有权的基础。中国自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制便占主导地位。秦汉以降,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虽遇周折,但至宋时已深化至很高的程度。土地的市场要素与产品要素日显突出与扩大。如果说,土地是中国社会人们最大的财富与财产的话,那么房屋作为“业”也是私有财产制的重要内容。宋代文献中,“田宅”是法官审理民事案件最常用的词汇,因此,田宅私有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就价值追求的基础以及由之而生的公私观念而言,传统中国与西方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传统中国社会中,不可能出现绝对私有的财产制度,在现实中国中,这一制度也是难以实现的。在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下,虽然个人“权利”及个人私产会受到官府与社会的压制,但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土地私有制度。⑥传统中国社会确实产生了商品经济,发展出了土地的商品属性和交易属性,普通百姓也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个体性质的生存、生活需求以及相关的利益诉求,因而基于传统中国的历史事实,宋代作为商品经济和世俗文化尤其发达的时代,土地私有制确实成为了社会经济的主要形态。
宋代土地所有制分国有与私有。国有土地有营田、屯田、弓箭手田、马监牧地、官田、学田等,称“公田”。⑦“公田”与“民田”相对,宋赋税的记载便有“公田之赋”与“民田之赋”的差别。⑧
据著名宋史专家漆侠先生之研究。宋代的土地私有制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他说:“在宋代土地所有制中,土地私有制占绝对的支配地位。”他进一步论证道:“北宋垦田在宋神宗熙宁元丰之际最高达七百万顷,可能在七百五十万顷左右。由此可见私有土地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⑨
对宋代土地私有制的深入发展及史料中诸种反映土地私有的社会现象,笔者以为可遵循下列线索加以分析。其一,土地私有的本质特征是自由买卖。宋代,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流通的方式有多种。一曰典,二曰卖,三曰指名质举,四曰倚当。与唐相比,宋代土地私有制深化的程度在土地权能的细化上,尤为突出。唐初,国家实行“均田制”,即国家授受制。唐把土地分为“口分田”与“永业田”两大类。原则上,“永业田”可以附条件的买卖。“口分田”一般不准买卖,特殊情况下可以买卖。⑩可见,唐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既多又严。宋时,这种限制全然不存。土地既可绝卖,亦可先典后卖,还可只典不卖,甚至以田宅作质押,以折抵因主债务而产生的利息,宋代称为“倚当”。(11)由田宅流通与处分所引起的诉讼纠纷,官府称为“田宅之讼”,无日无之。
其二,就宋代的田土与户等关系而言。宋代的户等,既有主客之分,也有“五等”划分之别。就“主客之分”而论,宋代把有土地的田户称为“主户”,无土地的人户称为“客户”。主户占人口的大多数;就“户等”而言,宋把有土地的人户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为地主阶级,四五等户为有土地的农民,这类户口在宋代占据了极高的比例。漆侠先生指出,在宋代户口中,拥有土地的农民属于其主体,而五等户中,四五等户又占43.3%~58.5%。(12)
其三,富户的田产可作为女儿出嫁之奁产。宋代笔记中就有反映南宋婚帖具体内容的史料,其中就分列了“房奁”的构成内容。(13)《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卷八《女合承分》记载:南宋人郑应辰有两个女儿,无亲生儿子,后过继了一个儿子。即养子。郑应辰在世时,“家有田三千,库一十座。应辰存日,二女各遗嘱田一百三十亩,库一座与之。”郑去世后,养子欲独吞家产,受到了法官的斥责,审理者依遗嘱给两女儿每人130亩田产。这在《清明集》中并非孤例。
其四,宋代的“女户”也是私有土地者。所谓“女户”,是指家无男丁由妇女担任户主的民户。马端林说:“凡有夫有子,不得为女户。无夫、子,则生为女户,死为绝户。”(14)女户作为独立的户籍,意味着它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缴纳赋税则以具有田产为基础,因此“女户”必具有私人田产。(15)
私有制上升为权利,须由法律加以规定。以现代法学言之,法律依其规范的性质与调整对象之不同,可分为公法与私法两大类;又依其成文与否,可分为成文法与习惯两大类。宋代,尚无现代法学之理念,故法律编纂的体例与体系中,虽无单独的私法系统——民法典,但却在成文律典令典及单行法律规范中都有现代民事性质的规范。
以宋朝一代大法《宋刑统》而论,不仅其中的“户婚”“杂”篇中有民事规范,这被现代学者称为“刑法典中的民事有效”部分,且它还在《唐律疏议》的基础上增添了四项内容。(1)“务限法”:专门受理民事案件的条款。(2)“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有关田宅典、卖、指押、倚当的法律。(3)死商钱物:外籍商人在中国经商死后财产如何处理的条款。(4)户绝资产:指无子嗣之家财产如何分配的法律。(16)这四个条款既涉及民事程序,也涉及田宅交易、外商财产处置、遗嘱继承诸民事领域,是纯粹的民事条款,这是律。再就令典而言,中华法系常以“律令体系”著称。说中华法系是律令体系,并非否定礼在古典中国法律体系中的支配作用。而只是说律典与令典都是成文法典。对律典,学界已耳闻能详,因为自《唐律疏议》之后,我国古代律典皆完整地保留下来,譬如《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而令典早已散佚,人们难以睹其真容,只是通过文献记载知其大概而已。1999年,宋史专家戴建国于“天一阁”发现“明钞本天圣令”,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宋史专家以此版本为研究对象,组成课题组,经几年整理研究,出版了《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令复原研究》一书。(17)
《天圣令》虽为残卷,但其发现既为我们认识唐宋令典的面貌提供了实态,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古代的法典编纂体例与体系,不单纯是以刑为主的律典,还有不以刑罚惩治为手段的令典。《天圣令》中的“田令、赋役令、关市令、丧葬令、杂令”都是民事法规,或者是相当于现在的特别民事法规。(18)
除律典、令典外,宋代还有以敕令形式颁布的单行民事法规或商事法规。著名者如宋仁宗天圣四年七月颁布的《户绝条贯》及其进行海外贸易的《市舶条法》等。(19)
此外,宋代的敕令、砧基薄、省薄、鱼鳞图册与田宅契约文书在田宅的归属与流转中,发挥着现代民法的物权、债权功能。(20)除敕令外,也在司法审判中发挥着证据的作用。
由于史料的繁杂,加上宋代尚无现代的民法编纂体系。因此,以法学的视野对其私有权能分类,是有一定困难的。但又不得不做尝试性努力,因为若不以今人的眼光看待历史,以现代法理分梳宋代私有权的历史事实,我们的研究与认识将无法深入,对现代的读者也无法对话。
欲将宋代私有权进行分类,首先是确定分类的标准,其次是对有关史料的选择与归纳。先言分类标准,若以财产的物质形态可否移动为据,私有财产权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即不动产私有权,也就是田宅所有权与动产所有权,如牛马驴骡驼、车船及生活用品。
若以现代民法理论为据,把具有财产权诸项事实要素与功能要素加以提炼,而不是仅限于单纯的概念所指的话,那么宋代的私有财产权仍可大体上分为物权、准物权、债权、继承权、抚养权、养老权等。实际上,无论古今中西,想要对财产权进行精确的定义与分类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而理论与概念又无法穷尽社会生活诸现象。我们在使用这些理论分析宋代事实时,需要有着足够的警醒,防止生搬硬套,更不能远离宋代历史场景,臆解历史,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二、宋代律典、敕令与经义对私有权的规制与支撑
现代法治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规制与保护,主要是在宪政的框架下,分别以部门法的形式而进行的。(21)
一般而言,首先,往往会通过宪法或其原则宣告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其次,民法典及其民事关系法规,会在民事权利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的原则上,把民事主体对物支配、占有的财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纳入到权利、义务的框架中,通过授权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规制各类私有权能,如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也会把人与人之间形成的身份关系、财产继承关系、抚养关系,通过权利义务关系的理论而创制成为婚姻家庭制度,使亲属、继承独立成篇而编纂于法典之中。民法典编纂及其关系法规的制定,是现代法律体系支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强大支柱。最后以刑事制裁的严厉手段,通过对犯罪人的惩处而保护所有人的私有财产权利。
宋代的法律不同于现代,但其所具有的功能及其对私有权维护与规制的历史事实,仍不妨以此眼光,进行有层次的分梳。不过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宋代没有私法体系与民法典编纂,对私有权的维护与规制自然有着自身的特点。
第一,通过敕令与经义的升格,使民众获得恒产——田宅所有权。在古代,儒家经典在治国理政中具有宪法的功能与地位,礼治原则就是国家的宪纲。(22)《孟子》作为儒家经典,在宋代由“子部”升格为“经部”,从此入“十三经”,其重要原因有二。一是五代十国以来,斯文扫地,武人当政,宋朝统治者要重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孟子作为孔子伦理思想的最大继承者,其仁政仁爱思想自然会受到青睐。二是在《孟子》一书中,“有恒产”才有“恒心”的思想,完全适应了宋代田宅私有化的浪潮,经大儒朱熹系统整理,直接影响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两宋之时,拥有一块土地的农民占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虽然《孟子》入经在南宋,但重视经义在治国理政乃至立法与司法中的作用,则是自宋初就已开始了。
宋建国之初,从宋太祖到太宗的三十八年间,朝廷颁布无数道敕令,鼓励农民种桑植树,开垦荒田,振兴农业生产,并庄重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现举数例如下,以资说明。
(1)太祖乾德四年曾有诏书专门对广泛垦殖的农户进行奖励。(23)
诏令中的“通检”是普遍查索,调查之意。在这里意在强调:国家承认农民对新垦荒地拥有私有权。通过开垦荒地而取得所有权是宋代土地私有权确立的一种重要形式,宋初对开垦荒地实行开放、自由、鼓励的政策,很多无地的客户通过这种形式获得土地,而上升为主户。我们再看下面一道诏令。(24)
(2)太平兴国年间,宋太祖为了劝课农桑,曾专门下达诏书,在民间选拔“农师”,给予一定的奖励措施,使之在民间农业生产中起到引导、督促农业生产恢复与扩大的作用。(25)
宋初三十余年间,因受唐中期以来战乱影响,尤其五代十国时期,兵火连年,民不聊生,大片农田因人口流离抛荒。人稀地广,旷田片片。此种形势下,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朝廷不得不采取多种措施,通过诏令的形式或鼓励开荒,或约束流民归业,(26)或招募民众通过佃耕而取得土地私有权。
(3)宋太祖为了推动恢复农业生产、鼓励百姓开垦荒田,曾经专门下达诏书对新开垦的荒田予以确认,并规定这些新垦田地能够成为开垦者的“永业”。(27)
“业”在中国古代是个专有名词,大多数情况下指田宅,有时亦指生活用品。当用作“管业”与“永业”时,多指田宅,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不动产。“为永业”即是这块土地为开垦者或耕种者永远所有,意义如同现在所说的所有权,又有所不同。(28)
经义与敕令的价值位阶,如同现在的宪法与政策,是中国历史文化条件下,土地私有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的特有制度。
第二,通过律典规制田宅所有权转移的方式,对违法者,律典或敕令给予制裁,以保护私人所有权与田宅交易的秩序。
这里必须说明两点。首先,与唐相比,宋代的土地买卖、出典、倚当已是遵循经济规律,依照社会生活需要,根据当事人意愿而自由进行,(29)不需要向官府请牒立帐。土地上的负担因赋税之需,自然不能免除,但买卖上的限制却越来越少,基本上是自由典卖、卖、倚当。所以契约任由私人签订,官方并不强加干预,这是要首先申明的。
但是,田宅毕竟不是一般生活用品。它们不但能给人们衣食之源与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而且对它们的利用还牵涉到国家的赋税与邻里、亲戚的相关利益。故它们的交易不可能像小件物品那样完成。这在今天也是如此。宋代,在承认土地私有,买卖自由的大原则下,国家对田宅的交易,即物权的转移、利用、过割还规定了一套完备的程序。另外,田宅交易或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违反者就要受到刑事制裁,以保障私有权益与交易的安全,这在法典与法令中有详尽的规定,现分述之。
其一,买卖双方当事人据意愿,确定交易形式,或典或卖,或倚当,在中间人见证下进行。这在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间即已确立,(30)宋代自然沿袭。《袁氏世范》中就专门记载了这一阶段的交易习惯与程序,提到了寻找中间人、表达交易意向以及确认交易对象的内容。(31)
其二,“典卖田宅,先问房亲,次问四邻,房亲不要,他人并得交易。”(32)之所以有此类规定,一是受伦理道德制约,田宅交易不出族;二是,农业社会,守望相助。田宅周围之乡亲四邻,若是本宗亲属,便于扶危济困。当然如此规定,也会有问题,如房亲四邻借此压价,或拖延时间,均影响田宅交易的经济生活本能及交易效率。对此,宋代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平衡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二者的关系。
《文献通考》记载了宋哲宗时期的一项动议,要求沿用旧法,限定行使亲邻权利的行为必须同时满足亲、邻两个要件,(33)即明确限定有服亲决定是否参与交易的期限,以防拖延、影响交易。到了南宋时,问亲邻之法,限制在既有亲也有邻的范围内,有亲无邻,有邻无亲,皆不在亲邻法调整之内,这是因为,交易中引起的诉讼纠纷常常使司法机关十分烦恼。法官胡颖的文书中就专门记录和描述了因亲邻问题而产生的交易诉讼实况,并专门在文书引述了“庆元重修田令”与“嘉定十年刑部颁降条册”,指出亲、邻两者属性兼具,是实行亲邻法调整的前提。(34)
其三,双方当事人、中间人评议价格是契约签订之基础。三面评价(即要价、出价、估价),是宋代田宅典卖土地的常用语。比如南宋时期的契约文书中,就有“三面评值”的说法。(35)
其四,写立合同契约,双方当事人、见证人签字画押。田宅交易在宋代,本由当事人自愿,故所立契约,原无统一格式,这当然反映了田宅作为私有财产,其买卖是自由的。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私立契约,往往对所交易之田宅的范围四至不做清楚交代,邻里也不知悉,遂致弊窦丛生,争讼日繁。为此,太宗采纳了开封司录参军赵孚的建议,确立了“割移”“典卖”这两式契约文书的范例。(36)
这只是说,官府颁立一个合同样本,当事人定约时,可模仿此格式进行,并非是官府印制的统一的标准契约样本。在宋真宗时期(乾兴元年,即公元1022年),朝廷依从地方官员的建议,正式确立了合同契法,专门规定了田宅出典活动中,契约文书必须一式四份,分别交由交易双方、商税院及地方官府保存,以此作为交易的凭证,目的就在于消弭因契约不明而导致的纠纷问题。(37)
由于宋代土地、田宅的典与卖已是社会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兴讼纠纷自不可免。官府出于税收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角度,试图统一契约格式与标准,其主观愿望不能说不好,但在客观效果上,并不一定能达到上述目的。因为统一的格式不便于民间田宅交易。宋哲宗时,已开始松动,到了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这一做法受到户部员外郎马骐的批评。(38)后朝廷认可:田宅交易,契约签立,除了必须有牙保、写契约人亲书押字、标明四至、到官府投税印契外,其他格式一律松动,由民间自由掌握。
其五,投税印契,官给凭由,对行批凿砧基簿,办理过割手续后,交易才算完成。田宅作为大宗商品,不论是典与倚当,或者是卖,都牵涉到该私有财产上的使用权益与所有权益,即现在所说的用益物权与物权,还牵涉到户等的升降与国家税赋的征收。故这种交易虽是在田宅可自由交易的大原则下进行的,法律法令主旨自然是规制田宅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维护当事人私有财产权,这是自不待言的。但田宅各种形式的交易,无不关涉到户等升降与国家税收落实。因此,宋代政府严令双方当事人必须在一定的时限内,或两个月,或三五日,到官府一般是县衙门,办理交税凭证。且要携带田宅底册——砧基簿,当厅批对,即将田宅数目从买方底册中除去,转移到卖方底册上。宋代文献中,前者叫“投印交税,官给凭由”(即常说的盖有官方印章的契约文书——红契);后者叫“双方批对砧基簿”。
正常情况下,经历上述五道手续,或者说五个步骤,田宅交易才算完成。可见,田宅作为不动产,无论中西古今,其使用权与所有权的规制都是要经过一套完备而又严格的程序的。(39)
其次,田宅的各类交易既然是儒家伦理语境下进行的,那么父死母在的情况下,儿子即便成年为家长,当他进行典卖田宅时,母亲对家产仍有监护权。因此,必须获得母亲同意,才能交易。否则就是违法,要受法律惩罚。“子之鬻产,必问其母”既是宋代的法律原则,亦是宋代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价值的共识,更是法官的判案依据。(40)宋人程迥说:“母在子孙不得有私财”。(41)对于怂恿子弟分产或故意使子弟负债以谋其家产的人,刑罚是流配。对此,台湾著名宋史专家柳立言先生曾有论述。(42)
第三,通过令典规制牛马等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形式;对于一般财物、麦粟的出举(月息不得过六分),“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不加干涉)”;对于拾遗物、宿藏物、漂流物则注重平衡国家、原物主及拾得人三方权利的平衡。
其二,对拾遗物、漂流物、宿藏物的规制,原则上既保护原物主的私权,又根据拾遗人或者漂流物拾得者是否付出代价而给予不同份额的报酬,这种平衡理念,体现了法律的公平精神。
《宋令》就有相关规定,对漂流物、宿藏物拾得行为进行了区分情形的确认。对于拾得漂流物的行为,要求首先在发生地对物品拾得进行公开并报告官府,有物主认领的情形下,拾得者能够获得拾得物品的部分利益,没有物主认领的情形下,物品归拾得人所有。对于拾得宿藏物的行为,在公共地域发现的物品,归拾得人所有;在他人私有地域发现的物品,则由拾得人与地域所有者平均分享。(43)
“漂流物”,是指江河发水时冲击下来的竹木,牛马或其他有经济价值的物品。这些物品或原有主人或没有主人。河流中捡拾漂流物与路上拾遗不同。后者不须付出代价,前者须投入相当大的气力,甚至冒生命危险。故法律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份额的报酬。若是有主人且在设置期限内认领的,大份额归原主,小份额归拾得者。无人认领,归拾得者所有。
“宿藏物”,即埋在地下有价值的物品或“形制异者”之古器(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物)。若发现地点在官地内,皆归发现人所有。这些发现人绝大多数是佃耕官田的人户,官府不与其争利。若于私地发现,须与原田主平分。若是具有文物价值的器皿,则物归国家,由官府发给报酬。宋代法律承唐之精神,把拾遗物中的宝、印、符、节与马、牛、羊等称为“阑遗物”。(44)“阑遗物”与“漂流物”之规制,既有律典也有令典,不同的是前者有罚则,后者则无。法律的这种规制,用现代民法理论分析,颇似“无因管理”,但古人法典、令典所体现的保护私权,维护公平正义的理念则是与现代民法颇为契合的。
其三,对于一般生活用品之债权,《令典》之规制原则上尊重私人意愿,自订签约,约定利息,官府并不加干涉。但利息(月息)最高不得过六分,积利不得过一倍。若债务人逃跑,则由保人代偿。(45)
对于特定的债务形态,《令典》也有相关规定,如以粮食出借形式产生的债务,允许以粮食形式归还。(46)令文中的“官不为理”,就是遵从当事人意愿,官方不加干涉之意。当然,若债主契外强制胁迫别人财产,追夺利息,则是不允许的,官府则加以干预。
其四,关于财产继承,宋令也确认了遗产继承的位序高于法定的顺位继承。这一点,宋令是与唐宋律典精神相一致的。在“户绝”的情形下,被继承者在世时已经订有遗嘱的,其内容在原则上可以排除法定的顺位继承。(47)
对照《宋刑统》卷十二《户绝资产》《丧葬令》条,这条《天圣令》条文与唐《丧葬令》几乎相同,说明宋《天圣令》来源于《丧葬令》。依宋令,女子依婚姻与否,分为在室女与出嫁女。前者为未婚,后者为已婚。对于家庭财产,法律规定的原则是:诸子均分。(48)若身丧户绝,又无嗣子,则除去丧葬费用外,财产由在室女继承,无女者,依次归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即归政府)。如果,被继承者生前立有遗嘱,经查核属实者,则依遗嘱。这说明,宋令规定了有条件的遗嘱继承。这个限制条件是,只是户绝资产才实行遗嘱继承。
三、宋代司法对私有权的保护
如果说敕令、律典、令典只是从立法角度对宋代社会生活中的私有财产权,如田宅所有权、牛马牲畜及生活用品私有权、户绝资产中遗嘱继承权等,进行了规制的话。那么私有财产权一旦进入流转程序,在社会生活中就难免会发生各种形态的纠纷。对此,宋代法官又是怎样来保护私有财产的呢?
现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据,结合其他历史文献,从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特殊群体,即具有某种特殊身份的人出发,来考察宋代司法对私有权保护的法律实践,以深化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譬如私奴婢中的“女使”,社会生活中的“赘婿”等,便是切入点。
宋代,随着私有制的深入发展及社会关系的变化,唐律中的良贱之分,及奴婢、部曲对主人身份依赖关系,已有较大的松动。尽管官奴婢终宋之世,也没有废弃。但由于宋代经常大赦旧的官奴婢,新的官奴婢因犯“三逆”者人数不多而减少,故学界并未把宋之官奴婢视为重大问题,而宋人反把唐视之为贱民的官奴婢——“官户”上升为官宦之家,可知变化之巨。(49)
私奴婢的身份有两种,一是女使,二是人力。与唐相比,宋代的私人奴婢已由贱民上升为良民。柳立言先生说:“尽管宋人和我们继续使用‘奴婢’来指称私家仆婢,但已非法律名词,而仅是泛称,‘贱’字也一样,大都作为形容词。在法律上,男仆称‘人力’,女婢称‘女使’。”(50)若是良民因生活所需,为别人打工或干家务,五年后可视为同居卑幼,受同居法律的保护。法律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利,防止他们无奴隶之名而有奴隶之实。规定雇主与他们签定协议——即契约,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年,期满可自由离开;他们可以由旧主转雇给新主,但不能卖给新主。报酬无着落,他们虽不能直接告主人,但可以由家人代诉;他们不顺从,雇主不得行私刑,尤其是刺字,而是要报官;主人犯罪,他们不受株连。当然,私奴婢与主人不可能在法律上完全平等,如主人与女使发生性行为,通常不被视为有罪等,反过来,男奴婢一人力若强奸或和奸主人的家人,虽然双方都是良民,但人力刑罚重于凡人。(51)
司法上,私奴婢中的“女使”所具有的私人财产权利是否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我们看宋人判词《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一个案例。南宋年间,有个叫罗柄的男主人雇了一个女使,名字叫“来安”又名“阿邹”。在罗柄年老时,为罗柄生下一子,使罗柄得以免绝嗣之忧。然而,罗柄妻甚妒之,来安母子只好暂栖于外,依靠罗柄所拨田产生活。不料,孩子夭折,来安被遣送归己家与自己父母同住,田产交回罗家。不久,罗柄又把另外典到的一块田产赠送于来安,且以来安的名义立户。及至罗柄去世,罗夫人即刻派出幹人出庭告状,不但欲夺回罗柄所赠产业,更企图把来安自置的田产一并夺去。
对此,法官范应铃在判词中不仅严厉批驳了罗柄妻赵氏的歹毒,还判决来安胜诉,罗柄所赠田产及其利用这块田产购置的产业,统统归来安所有,且在来安再嫁人之时,为其自随田产。(52)
据台湾学者王平宇的研究,《清明集》中涉及女使的诉讼大体上有五类,即涉及家庭财产的诉讼、涉及遗腹子的诉讼、涉及奸淫的诉讼、涉及诬告的诉讼、涉及拐卖人口的诉讼。(53)财产类诉讼首当其冲。就《清明集》中所涉此类案件的审理来看,在仅有的五件案例中,有四例是法官依据书证与物证在查证案情,弄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女使胜诉的,这说明“女使”虽社会地位较低,且涉及家庭财产纠纷的关系复杂,但其合法权益还是得到了保证。(54)
那么,宋代法官是怎样审断此类案件的呢?再以上述案件为例。首先,法官是依据书证与物证来查清事实的。故重视书证与物证是南宋法官审理田宅之类案件的突出特征,这在《清明集》中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规律,占案件的90%以上。就“来安”一案而言,罗柄赠予女使来安的田产均有“省簿”(物证,即宋代官府保存的田产底册)与印契(即纳税的法律文书)。(55)
其次,是明辨是非。法官虽然在本案中维护了来安的合法权益,却没有支持她可以独立户籍。在宋代的法律中,女子只有在户绝或成为寡妇的情况下才能立户,时称“女户”。来安归家时,有生父邹明在,依据“同居必须共籍”之原则,来安不能自立门户,故法官判决罗柄赠于来安的田户只能归于其父名下,这是必须明确的。
最后,法官是依法判决的,并非都是基于同情的立场。(56)譬如,取消来安的非法户籍,就是依据法律规定的“父母在,子女不得别籍异财”;维护来安的私有财产权益,就是依据印契与“省簿”上来安的名字。案情中的罗柄赠给来安田产的“批帖”,实际上就是“遗嘱”。宋代律典与令典均承认民间所定契约只要是依法纳税,均具有合法性,官府所指定的契约样式只具有指导性而无强迫性,但纳税办理过割手续则具有强制力,遗嘱亦是具有合法性的。法官由此而做的判决不是依法判决,还能是什么。妄加指责,是人为的偏见,不是合理的怀疑。好在《清明集》判词俱在,读者不妨细读之。
再看法官对宋代社会生活中另一种具有特殊社会身份的人——赘婿,是怎么看待的,是否承认他们应得的财产权益?
“赘婿”在中国文化中是个有点贬义的词汇,俗称“倒插门”。“赘”字本身是多余的意思,“累赘”一词就是麻烦。赘婿,谓之“倒插门”,一是指不合儒家传统的传宗接代理念,二是会在生活中招致很多麻烦与纠纷。社会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致使倒插门的现象在宋代并非个别,而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法律中赘婿并非完全没有法律地位,而是权利受到伦理与习俗的各种限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二,元丰六年正月癸卯条称:“提举河北保甲司言:‘乞义子孙,舍居婿,随母子孙,接脚夫等,见为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亲属给半’。诏著为令。”(57)唐代法律关于赘婿如何分配家中财产尚无明确的规定,也没有与义务相连。(58)宋代,赘婿已非个别现象,入赘的现象已越来越多,故赘婿又有多种划分。现在由于文献的散佚,宋代赘婿的种类已无从考察。(59)大体上是说:“舍居婿比有分亲属给半”;而在入赘后,又有立继的情况下,赘婿以妻家财物营运,增产财产,至户绝日,给赘婿三分。
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两个有关“赘婿”的案例中,即卷七的《探阄立嗣》与《立继有据不为户绝》,法官都承认赘婿依法有私有财产权,司法应予以保护。但在实际判决中,又可根据案情适当平衡,给予不同份额。《探阄立嗣》一案中,虽主人家于户绝时由官府为之立继,但由于赘婿已“赘居年深,稽之条令,皆合均分”,故给赘婿一半。后一案例《立继有据不为户绝》,法官认为,赘婿虽依法应合得资产三分。但因赘婿已在嗣子成年分家时,从妻份中获得配额,且于尽孝礼节有亏,故不再给予救济。
其实,我们在考察宋代法律对私有财产的规制与保护时,已无必要从一般的历史事实与众所周知的共识上,论证宋人私有财产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是要深入到宋代社会生活深层结构中,譬如不同身份、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尤其是弱势的群体,如寡妇、婢女、接脚夫、赘婿等等,看宋代法官是怎样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证据厘清事实;依据经义解释法律,最后再依法保护其私有权的。因为若这些弱势群体的私有财产权都已受到关注,则一般民众的私有权受到保护不证自明。就赘婿而言,他们与“接脚夫”相似,都是特殊情况下到妻家的。前者是到已婚却不出嫁的女方家成家立业,乃至传宗接代;后者是到女子出嫁后丈夫亡故的男方家重组家庭。赘婿面对的是女方家的家族势力,后者面对的是男方的家族势力,家族势力往往在处理家庭财产的诉讼纠纷中影响到法官判决。家庭财产分割在此情况下是极其复杂的,往往会面临着家族势力背后的干预,宗法伦理的制约,世俗的成见,案件的复杂及其自身的情况。法律与伦理、习俗、势力诸因素是相互纠缠而难以厘清的。总体上说,宋代的立法与司法原则都是承认及保护这些弱势群体之私有财产权的。至于宋代的司法实践,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留下来的474个案例,504件判词来看,在涉及财产诉讼的“户婚”(即卷四至卷十)类中,财产争讼是主题。在这些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不仅遵循着保护私有财产的大原则,而且还因发生诉讼的当事人身份地位之不同,在依法判决的基础上,情理兼顾,注重用天理(多数是儒家经典所体现的义理精神及原则)补充法律,注重对卑幼及弱者的利益维护,这或许是大多数法官与朱熹理学思想相关,或许是与他们饱读儒家经典,有着高度的人文情怀及儒家仁爱思想的素质相关。至于司法实践中的诸种外力干涉及其司法遇到阻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再用力气加以讨论,本文不再赘述。
四、何种之私:西方法学理论的意义及其解释宋代私有权的限制
基于特定的传统中国伦理价值观念,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中的绝对私有制难以在传统中国与当下中国扎根。一般来说,中国的历史中,古典中国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的民法典,中国人没有私之神圣性的概念。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历史中没有土地私有制,立法与司法皆不保护与承认私有财产权。就宋代而言,虽然儒家主流价值观念仍然在支配着国家的法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土地私有制的深化,海外贸易的开展,都市文化与市民文化兴起,私的欲望与观念冲击着传统伦理道德的堤防,士大夫与一般民众并非都不言利,士人的婚姻与世俗生活都把“直取其财”作为时尚,宋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曾把宋代社会的新风尚用精确的语言概括为“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60)
尽管,私有欲望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会受到官府的压制及法律的惩处,但两宋社会又确实存在着国家、宗族、家庭等元素互相抱合又互相分离的特定土地私有制。在此情形下,宋代私有权及宋代私有现象,共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值得讨论,学界以往很少运用现代法学的理论对它进行厘清,或者进行适当的分梳,更没有指出其意义及其限制。
第一层,与国家相分离,“家庭财产私有权”的主体是“家”,即“家庭之私”。就此而言,两宋田产有“官田”(或称“公田”)与“民田”之分。“民田”在两宋社会生活中呈现出主导的特定地位。仔细推究,此时“私有”性质的民田,不同于西方基于个人本位而生的所有权之私,而是基于传统价值追求与生活原理而生的“家产”之私。这种“家产”之私,或曰“家庭私有财产权”,是以家、户为单位,以个人名义而进行交易的家庭私有,其主导的观念与制度都基于“父权”和“家长”。这种权利可以继承,也可以进行交易,如田宅的典、卖、倚当、租佃等。这层意义上的私有权,既在物质形态上称“民田”或“私田”从而与“官田”相对应;同时,又在权利功能或价值形态上承担着国家的赋税与伦理观念的制约,如家族对田地交易的优先权,共同构成家庭私有财产权上的负担,承载着缴纳赋税、稳定家族和睦、敦化风俗的多重社会功能,是中国社会也是宋代社会生活中独具时代与民族特色的私有权。
申言之,这层财产意义上的私田与公田相对,大量存在于宋代百姓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可于宋代历史文献中发现大量以个人名义处置、使用、占有土地的大量案例与事实。这自然是私,也是个人行使田宅私有权的表现形式,是与公田不同的个人之私。此种个人之私,不同于现代西方语境下的个人之私,乃因为两者对于“个人”的不同理解。在现代西方法学理论看来,“个人”仅指个体,并不附有任何与他人共享利益的内容;而在传统中国伦理下的“个人”,不单单包含了现代独立“个人利益”的意义,在“个人利益”的内容之中,附着有个体必然的价值追求——家庭伦理,或者说,中国传统的“个人利益”,其内容中就有指向家庭成员的“他人利益”。在家庭伦理(主要是“养父母、蓄妻子”)作用下,即便身为独立个体,其内在利益诉求就包含了保证家庭成员生存、生活有所依靠。在这一附着家庭伦理的个体之私的观念支配下,个人交易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家庭成员利益的内容,因而两宋个体之私,在其产生与行进的过程中,往往隐含着家庭生活理念与“同居共财”的制度。共财并非是“共同所有”,因为它没有西方民法理论的权利主体观念,家庭成员之间并非独立的个人主体,而是以父权占主导的家庭共有。田宅所有权的主体是“家”或“户”。对此,俞江教授有过精彩的分析与论述。(61)
第二层,是外商财产的个人之私。唐宋时期,宋代更加突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大量外国商人来到中国经商,随后在中国安家,结婚生子,置办产业,他们在中国生活下来,史称“住唐”。外商死后的财产如何处理,唐与宋皆制定了专门的法令,这就是《宋刑统·户婚门》中的“死商钱物”条款。从这些条款来看,死商之人在中国的财产,若有家人亲属相随,给付家人亲属,如无人相随,官府代管。其父子兄弟来中国相认,经查证属实者,也令官府给付。由于外商家庭情况的复杂,法令总的原则是相随亲属都有继承权,有血缘关系的中国亲属也同样具有继承权利。死商的寡妻无子女者,在室姊妹、出嫁亲女也同样有三分之一财产权利。这种私有权,既原则上遵循中国的文化精神,又适当给予变通,也是一种特有私权之类型。(62)
第三,伦理个体之私。在重视家庭纽带、强调孝悌的儒家伦理背景下,抽离个体地位、整合家庭主体性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主流地位。就这样的主流情境而言,个人之私往往被家庭伦理所抑制,“家庭成员个体之私”的产生与成长似乎难以实现。然而考察传统价值观中的两项内容,却能够解释为何在这样一个看似压抑的条件下,个体之私得以出现并获得承认。其一,传统儒家在强调与他者相联结的社会伦理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个人独立品格的个体伦理。比如孟子归纳了个人面对“威武”“富贵”及“贫贱”的三种情形,并提出了相应的独立人格追求。其二,经济形态的演进与日常生活的实在需求,使得功利主义不可避免地产生,在这样的世风下,理想性质的人伦道德必然受到挑战。在这一社会发展的条件下,统治者很难完全无视现实,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成员个体之私”进行承认。宋代的“家庭成员个体之私”,在社会中的表现有五种:A.“厚奁之风”下的妇女奁产制——即妻子的嫁妆;B.生分(分家)时,诸产所得之财;C.父母的养老田;D.继子或赘婿的财产继承权;E.宋仁宗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政府允许儿子因白手兴家或仕宦所得的财富作为个人的私财。
这种内生性的个体之私,完全基于传统的孝义价值观,实际上是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对孝义价值观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实践理性基础上对人伦存续规律的认识深化,异于西方个人权利的“觉醒”。具体说来,所谓伦理个体之私,有五种含义。第一,我们必须承认在古典中国以儒家文化重家庭尚孝道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仍存在个人之私生长的空间,尽管它随时受到社会舆论、伦理道德、政府法令的三种挤压,但依然在宋代社会空前活跃。第二,这种私不同于西方近现代社会出现的个人本位之私或个人权利之私。为何如此说,这是因为田宅的私有买卖尽管以个人名义进行,但是它在交易时,往往有乡规俗例进行约束,有所谓“田不出族”之说。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点,即亲邻优先权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田宅交易中的一项原则与传统。第四,尽管妇女的奁产可不入家产的范围,并在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判例中多有实例,且获得司法的支持,但当夫死改嫁时,这份财产仍受“妇同夫为主”之法令及伦理因素的限制,有时会不受支持。第五,这种私在宋代社会生活及司法实践中虽得到司法保护,但主要是靠法官对案情的认知而进行的。在复杂的伦理关系网络中,权利的模糊性仍在所难免。
从历史实证的角度看,宋代法律传统在立法、司法及对乡俗惯例的默认三个方面对上述三种“私有财产权”进行着保护,以求达成适应社会发展、引导社会进步的目标。其具体表现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立国之初,创立者就下达诏令,明确承认和肯定了土地私有制现象,给出“不立田制,土地得自由买卖”的政策。其二,在基本法典层面,《宋刑统》中有诸多条文的目的在于保护业已存在的“私有财产”。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继续沿此历史轨迹行进。其三,在司法层面,统治者和法官都注重田宅细故的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也都务求保护百姓的私有财产,甚至于对低下阶层的“杂人”“女使”的财产都予以承认和保护。这一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分外耀眼。其四,再从判例上看,法官们对于乡规俗约背景下产生的私有财产保护机制,也是予以默认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认识宋代土地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时,不能步入这样一个误区:国家制定法是土地私有制及其保护的唯一根据。对于宋代以后的明清社会,土地私有制在法律体系、规则体系中的潜在内容与隐含意义必须纳入视野。
(1)刑律往往通过明确责任划分、限制加害行为的方式,达到保护合法私有权益的目的;在法律条文的表达上,通常都是注重对加害行为的规制。其背后隐含的价值规范,自然就是对个人私产的当然确认与保护。这样的法律体裁,以责任划分、制止损害为中心,并不直接从正面细致罗列私产的权益内容,自然不可能产生正面规定物权内容的“物权法”。
(2)契约文书在中国法律传统中,起到证明物权债权存在、细化物权债权内容的载体作用。受现代西方法律体系及其文本影响,契约往往只是单纯地被视为证据。但在中国历史的事实中,契约在证据属性以外,兼具更深远的规则载体属性。由于中国文字系统较早成熟、纸张获取便利,渗透于官方、民间的规则意识能够便利地以物质形态出现(即契约文书),这与西方的历史事实有着明显的不同。契约文书的内容,虽然在文本论述上以物权、债权内容为中心,使得其首先成为证明物权、债权存在及明确其内容的证据,但在其诉求表达的背后,无不表露出物权、债权得以成立的规则基础。契约文书在财产流转过程中产生,其所依赖的流转规则乃至民事活动、社会互动的“常理”,就是支配其行文、表达的原则。从这一层面看,契约文书不单单是证据,同时也是规则的物化表现,亦即规则本身。
(3)乡规、民间交易习惯对于民间财产交易活动(其核心内容主要就是田宅土地)及相关诉讼、审判,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调整作用。反映两宋田宅交易的原始材料中,如《会要》体文献中的相关内容及《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田宅书判之中,已经对“乡源惯例”的存在作出确认和肯定。
(4)将传统中国特殊形态的私有制度转化为私有财产权利,需要通过法律进行界定。按照现代法律体系,民法与刑法构成了对私有财产正反面的确认与保护,但在传统中国,这样明确的确权机制是不存在的。若简单地将西方法律体系移植到中国,而无视中国原生的观念、制度土壤,往往就会导致新秩序无法完全建立、旧秩序丧失活力、社会最终失序的局面。因此,在借鉴现代西方法典体例、法学理论的同时,不能遗忘根植于传统中国土壤的法律逻辑与生活原理,不能忽略古今传统的对接。
五、结语
文章的结束,不能不回答学界,尤其是长期受西方法学理论支配的法学界的质疑:即儒家语境下,宋代何以会生长出私有制与私有财产权利的空间与法律保护的历史事实。然后再指出用西方民法理论透视中国历史的意义与局限。
学界通常认为:儒家主流价值观念中的义利观与宗法伦理是制约私有制与私有财产权利产生、发展的严重障碍,甚至完全否定私有制及私有权存在及保护的历史事实。其实这种看法基本是在近代西方文明冲击下,以西方“个人主义”为本位而观察中国文化与历史时所形成的偏见,更是丧失文化自信心的表现。之所以如此说,理由在于三点。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儒家主流价值观念中的“义高于利”,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利存在的正当性。孔子主张以正当手段取得利益,即便是宋明理学的代表者朱熹也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饱食暖衣为正常之需,只是过分追求锦衣玉食,才是与天理对峙的“人欲”,须加以节制乃至消灭。其次,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反映在民事生活的规制上,固然形成了田宅交易中私有财产权的负担,如“亲邻优先购买权”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民事权利主体”形成的障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儒家仁政理念下的鲜活历史进程中,以家为单位的“伦理个体”,不但在民事行为中有着自己利益的诉求,且在司法实践中,那些著名的法官,即《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名公”们,还会以积极的态度,保护这个“个体”的利益诉求,甚至即使对那些弱势群体,如寡妇、女使、赘婿、接脚夫,也予以司法救济。这就告诉我们,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学理论的概念去裁剪历史事实——理论只是指引,不是僵死的教条。最后,必须申明的是,宋代作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中的近世,其假说并不被中国大陆学界所认同,但这个假说对宋代社会结构内部的变化及其社会诸领域的社会变迁,所具有的解释力与洞察力,则是不容置疑的。说到底,宋代社会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士大夫”趋向功利的士风、市民社会通俗文化及都市文化的利益多元化潮流,都在冲击着传统伦理道德的堤坝,孕育着私有财产权的产生,也为立法、司法对私有财产权的规制与保护,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总之,本文的结论有如下三点。
其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临的挑战既来自于实践,也来自于西方。在这样一个东西交汇、文明交流日益紧密的时代,无论任何领域的研究,都必须以现实的眼光对古今现象进行审视。在没有现代法学理论为参照物的条件下,研究者很难真正认识到中国法律传统的独特性质及其价值。
其二,对宋代社会而言,以田宅私有制为中心的财产权,既受儒家伦理观制约,也受反映时代之诉求的法律及司法保护。其保护的个体之私表现为“家产之私”与“伦理个体之私”。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这与现代西方法学理论的“绝对私有制”有明显差异。这个“私”非西方文化个体权利之“私”,而是中国文化中伦理个体之“私”。“私”与“私”逻辑起点不同,理论预设不同,故法律规范体系不同,价值亦不同,法秩序的形态也有差异。这个逻辑起点的差异全在于对人之本质属性的不同理解。
其三,西方法学理论只能为我们提供认识宋代司法传统的视野与方法,而不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教条。温情与审慎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律史应有的立场。
注释:
①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宋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志英:《宋代物权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参见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5-442页;另,亦可见台湾“中研院”“宋代法律和社会”研究人员自述。该观点的详细阐释,参见柳立言:《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载《唐研究》(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参见戴建国:《从佃户到田面主: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戴建国:《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日本学者的研讨,可参见高桥芳郎《:宋代官田的“立价交佃”和“一田两主制”》,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④参见程民生:《论宋代私有财产权》,载《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学者从不同角度涉及此问题的研讨,不再一一列出。
⑤关注中国古代私有财产权,是笔者长期以来研读中国法律史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笔者的硕士论文便以“元朝民事法规探微”为题,研讨元朝法律下的民事权利。20世纪90年代后笔者的研究转向宋代,2006年之后,欲集中运用《名公书判清明集》与《宋会要辑稿》等史料,分析宋代立法、司法对私有财产权的规制与保护,2011年撰写“何种之私:宋代法律私有财产权保护论略”一文。由于该文为论纲(约4000余字)故未发表。但文中的观点已以笔谈的形式发表于《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题目为《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重视从中华法制文明中寻求资源》。此提纲之思路,曾在“2011年西方法律思想史年会”、2013年7月于开封河南大学召开的“跨学科视野下的法律史研究”等学术会议上宣读。其中的部分观点以“汲取传统中国的法治资源”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4日评论版。
⑥著名经济史学者杨国桢先生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不是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它的内部结构是国家、乡族的两重共同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的结合。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的运动,表现为这几种互相结合又处于互相排斥状态的所有权之间在同一结构内地位的更替与消长。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私人所有权的发展,始终未能摆脱国家与乡族土地所有权的附着和制约。”参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
⑦宋代的“官田”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户绝田;(2)抛荒田;(3)“涂田”或称“泛长江涂田”;(4)国家籍没田。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8页。
⑧《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127:“宋制岁赋,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廓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曰杂要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15页。另外,“民田”之称亦可参见《宋会要辑稿》(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1页。
⑨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43页。在我看来,宋代的土地数量如同人口一样,史籍并无精确记载,只能估其大概。这是因为宋代的基本史料《宋史》《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三大史书中,“食货”“田赋”中并无历年土地开垦之详细数字。战乱时,土地之数字更无法精确,但漆先生顷毕生之心治宋代经济史,其所依据的史料达上千种之多,阅读范围之广,非一般学者所可企及,故所得之结论仍可为据。
⑩《唐律疏议》卷十二《卖口分田》:“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即应合卖者,不用此律。”疏议曰:“口分田,谓计口授之,非永业及居住园宅。辄卖者〈礼云〉‘田里不鬻’,谓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违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即应合卖者,谓永业田家贫卖供葬,及口分田卖充宅及碾磑,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准令并许卖之。”参见《唐律疏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11)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六《抵当》《倚当》。这部判词汇编所反映的宋代社会生活中的田宅买卖,典与当等,是极其生动的。对它的研究,可参见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另可参见郭建:《典权制度源流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2)漆侠先生说:“占有一块土地的农民,在宋代户口中占的比重极大。”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2-333页。
(13)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卷二十记载南宋的婚帖“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
(14)(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三《职役考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78页。
(15)在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役考》中,“女户”常与单丁,寺观等并列,说明“女户”家中无男丁,理应免役。但免役不意味着免田产之赋。
(16)参见《宋刑统》卷十二至卷十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6-207页。
(17)该书由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台湾大学历史系随即举办“天圣令读书班”,已发表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除上书外,大陆学界代表性成果有戴建国:《〈天圣令〉研究两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黄正建:《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台湾学者研究成果参见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18)具体内容,详见下面论述。
(19)“户绝条贯”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五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465页。宋代的“市舶条法”多以编敕的形式进行,《苏轼文集》收录最详。参见《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8-890页。亦可参见陈景良:《两宋海外贸易立法演变论略》,载《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20)参见尚平:《南宋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的关系》,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另可参见戴建国:《宋代的民田典卖与“一田两主制”》,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戴建国:《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1)这当然指的是成文法传统国家,英美法系是个例外。
(22)参见张千帆:《传统与现代:论“礼”的宪法学定性》,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南京师范大学主办),2000年10月。杜钢建:《梁启超论古代宪法与儒家宪政》,来源:http:/www.dtsx.org/article.php?id=597,2017年5月17日访问。
(23)乾德四年(公元966年)闰八月,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
(24)《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二《政事三十五》“农田”一目中所载之宋初诏令有十七种之多,皆是鼓励农垦,惩罚游手好闲,奖励辛勤,承认土地私有的法令。由此可见宋初朝廷对此一问题之重视。
(25)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闰年十二月庚戌诏:“民为邦本,食乃民天。常念稼穑之艰难,每虑田园之荒废。广兴山泽之利,大开衣食之源。既富庶之未臻,盖劝课之尤缺。宜令诸道州府,应部民有乏种及耕具人丁,许众共推择一人,练土地之宜,明种树之法,補为农师。令相视田亩沃瘠,及五种所宜,指言某处土地,宜植某物。某家有种,某户缺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三老里胥与农师共劝民,分于旷土种蒔。俟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常税外,免其它役。民家有嗜酒蒱博,怠于农务者,俾农师谨察之,闻于州县,寘其罪,以警游惰焉。所垦新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诏到宜亟行之,无或稽缓。”《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9页。
(26)诏令说:“应开封府管内百姓等,一昨霖霪作沴,水潦存臻,多稼即被于天灾,尽室不安于地著,遂致转徙,其将畴依。先是今年三月辛亥诏,应流民限半年复业,限满不见,即许乡里承佃,便为永业。又念民之常性,安土重迁。离去丘园,盖非获已。自今年十一月以前,因水潦逃移人户,任其归业,不得以辛亥诏书从事。”这是对前一道诏令的修订。准许因灾荒逃离家园的民户,在超过半年后,仍可回归家园,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但由此带来的冲突,即在辛亥诏令下,通过招佃耕种抛荒田地,而获得朝廷认可的民户,其权益如何平衡,这恐怕是个问题。宋廷怎么处理的,现在尚未看到史料之记载。诏令为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一月发布,载《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9页。
(27)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六月诏令说:“近年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汙莱。虽招诱之甚勤,而逋逃之未复,宜申劝课之令,更示蠲复之思。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与免三年租税,三年外输税十之三。应州县官吏、劝课居民垦田多少,并书于印纸,以俟旌赏。”见《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二,第659-660页。此道诏令又可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二册,第817-818页。
(28)这个不同点,详见下面详论。
(29)宋人袁采说:“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见《袁氏世范》卷下,《富家置产当存仁心》。
(30)参见(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31)《袁氏世范》卷下说:“人户交易,当先凭牙家索取阄书砧基,指出丘段围号,就问见佃人,有无界至交加,典卖重叠。”
(32)《宋刑统》卷十三载:“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7页)
(33)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五》称:“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臣僚言:〈元祐敕〉,典卖田宅,遍问四邻,乃于贪而急售者有害。乞用熙宁元丰法,不问邻以便之。应问邻者,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户内与所断田宅接者,仍限日以节其迟。”见(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3页。
(34)胡颖说:“照得所在百姓多不晓亲邻之法,往往以为亲自亲,邻自邻。执亲之说者,则凡是同关典卖之业,不问有邻无邻,皆欲收赎;执邻之说者,则凡是南北东西之邻,不问有亲无亲,亦欲取赎。殊不知在法所谓因问所亲邻者,止是问本宗有服纪亲之有邻至者。如有亲而无邻,与有邻而无亲,皆不在问限。见于庆元重修田令与嘉定十三年刑部颁降条册,昭然可考也。”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亲邻之法》。
(35)南宋淳佑十二年(公元1252年)徽州李从致卖山田契载:“归仁都李从致、从卿、侄思贤等,今自情愿将地名钱塘坞,系罪字号下山玖等拾玖号山肆亩,又民字拾壹号夏(下)田壹角贰拾步。其山东至胡文质地西至垄,南至屋口自众田,北至降。今来无钱支用,众议将前项四至内山并田出卖于同里人胡南仕名下。叁面评值,价钱拾捌界壹佰陆拾贯文省。其钱当立契日以(一)并交领足讫,不零少欠文分。其山地内即无新坟旧冢。今从出卖之后,已任买主闻官纳完,迁做风水收苗,永远为业。如有肆至不名(明),如有内外人占栏(拦),并是出产人祗(支)当,不涉受财之事。今恐人心无据。立此卖田山文字为照
淳佑拾贰年柒月十五李从政(押)
李从卿(押)
李思贤(押)
今于胡南仕名下领前项四至田山肆亩、田壹角贰拾步契内价钱拾捌界官会壹佰陆拾贯,前去足讫,并无少欠。别不立碎领,只此契后壹领为照。同前月日。从致(押)。
从卿(押)思贤(押)见交钱人李贵合(押)。”见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536页。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载:“孚(赵孚)又言:‘庄宅多有争讼,皆由衷私妄写文契,说界至则全无丈尺,昧邻里则不使闻知,欺罔肆行,狱讼增益。请下两京及诸道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人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本,立为榜样,违者论如法。’诏从之。”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42页。
(37)“乾兴元年正月,开封府言:‘人户典卖庄宅,立契二本,(一本)付钱主,一本纳商税院。年深整会,亲邻争占,多为钱主隐没契书。及问商税院,又检寻不见。今请晓示人户,应典卖倚当庄宅田土,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从之。”见《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464页。
(38)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户部员外郎马骐言:“窃谓典卖田宅,条令所载契要格式备矣,或不如式,在法,未尝不许执用。所有执用者准条明言违法,如私辄典卖之类,是诚不可以执用也。然则契要不如格式,非违法明矣,乌可不使之执用乎绍兴十年申明,将上件不依格式并无牙保写契人书字,并作违法断罪,不许执用;绍兴十九年宋贶申明:典卖田宅,不赍砧基簿对行批凿,并不理为交易。夫违法者,私辄典卖是也。今契内一项不如式及未批砧基簿,与私辄典卖情犯绝远,而一概以违法处之,则伦类不通,非所以为法也。”
户部看详(批示):“乞下敕令所检照旧法及申明、续降参照看详,颁降遵守施行。”本所看详:“‘旧来臣僚申请,乞今后人户典卖田产,若契内不开顷亩、间架、四邻所至、税租役钱,立契业主、邻人、牙保、写契人书字,并依违法典卖田宅断罪。难以革绝,交易不明,致生词讼之弊;不对批凿砧基簿,难以杜绝减落税钱及产去税存之弊。缘村民多是不晓法式,欲今后除契要不如式不系违法外,若无牙保写契人亲书押字,而不曾经官司投印者,并作违法,不许执用。已经投印者,止科不应为之罪。所有对行批凿砧基簿事,合依原降指挥施行。’从之。”《宋会要辑稿》(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473页。
(39)即便如此,宋代社会生活中,因田宅交易引起讼端的记载还是不绝于各类文献之中,这既是因为人心复杂,交易中伪造、欺诈手段花样翻新,更是因为田宅交易有关户等升降,而户等又与赋役制度密切相关,故实际生活中,有的人往往虚立契约,转移田产,降低户等,而达到逃役避税之目的,宋代称“诡名挟户”。由此引起的纠纷,两宋数百年间难以杜绝。参见《宋会要辑稿》(第12册),六一《民产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462-7474页。“诡名挟户”之案例,可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受人隐寄财产自辄出卖》。
(4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继母将养老田遗嘱与亲生女》。
(41)(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50页。也可参见《宋刑统》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
(42)参见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32-333页。
(43)《宋令》第14条规定:“诸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牒。有主识认着,江河五分赏二,余水五分赏一。非官物,限三十日外,无主认者,入所得人。官失者,不在赏限。”
《宋令》第26条:“诸以官地内得宿藏物者,皆入得人;于他人私地得者,与地主中分之。若得古器形制宜者,悉送官酬值。”见《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9-430页。
(44)参见《宋刑统》,薛梅卿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页。
(45)《宋令》第24、25条规定:“诸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亦不得回利为本。若违者积利,契外擎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断。收质者若计利过本不赎,所从私纳。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46)“诸以粟麦出举,还为粟麦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仍以一年为断,不得因旧本生利,又不得回利为本。”
(47)《宋令》第27条称:“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宅店、资财,令近亲(亲依本服,不以出降)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于女。(户虽同,资财先别者,亦依此。)无女均入依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即别敕有别者,从别敕。”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5页。
(48)《宋刑统》卷十二《卑幼私用财》条《准户令》:“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末娶妻者,别与聘财。故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见(宋)窦仪等:《宋刑统》,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7页。
(49)参见柳立言主编:《性别、宗教、种族、阶级与中国传统司法》“序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版。
(50)柳立言主编:《性别、宗教、种族、阶级与中国传统司法》“序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版。
(51)参见柳立言主编:《性别、宗教、种族、阶级与中国传统司法》“序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版。
(52)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罗柄女侍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
(53)参见宋代官箴研究会编:《宋代法律与社会——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14-236页。
(54)参见柳立言:《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下编),《身分:以妾为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9页。
(55)宋代往往把田产交易的一应契约文书与纳税凭证,统称为“干照”。参见陈景良:《释干照》,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56)学者中,有人认为法官是基于同情,才判决来安胜诉的。对比,柳立言给予了驳斥。参见柳立言:《宋代的宗教、身份与司法》,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8页正文与注释。
(5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009页。
(58)详尽的分析,参见邢铁:《唐宋时期妇女的分家权益》,载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6页。
(59)元人徐元端《吏学指南·婚姻》把赘婿分四种:(1)养老婿或入舍婿,即终身在女家,并改从女方姓氏,子女姓氏也随女方;(2)不改姓,待女方父母亡后携妻儿回原籍,留下一个儿子继承女方门户,称归家婿或舍居婿;(3)规定在女家的年限,年限一到,即另觅居处,称年限婿;(4)夫妻分住各自家中,称出舍婿。
(60)参见(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上册),《氏族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61)俞江:《家产制视野下的遗嘱》,载《法学》2010年第7期。另参见俞江:《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62)参见《宋刑统》卷十二。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沪)2017年第 3期